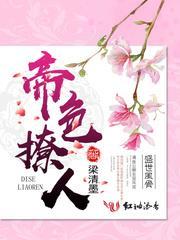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八零老太重生断亲,白眼狼傻眼了 > 第70章(第2页)
第70章(第2页)
两人走近,果然看见何秋兰双手叉腰,嗓子高得能炸瓦。
“你这秤不对!我明明买一斤半豆角,你这袋称出来连一斤二都不到!你就是坑人!”
那卖菜的小姑娘急得脸红,结结巴巴,“大姐,我这秤新换的,没短斤啊。”
“没短斤?你当我眼瞎?”
沈若棠看了一会儿,轻轻叹了口气。她走上前,“秋兰,你那秤是自己带的?”
“不是,人家供销社的。”
“那你哪看出来短斤?”
“我一抓就知道!”
沈若棠笑了,笑得不冷不热,“一抓就知道,那你比秤准啊。”
何秋兰一怔,“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多。”
“盐多嘴就咸,米多心才稳。你吃多了嘴咸,不代表理就在你这。”
人群笑出了声。何秋兰面子上挂不住,扯着嗓子,“沈嫂子,你少装好人。你以为你会说就能压我?我就是不信这称。”
“那好。”沈若棠看向旁边摊主,“老马,把你那秤借来。”
老马嘴角一抽,递过去。
沈若棠拿豆角重新称了一遍,秤杆一平,正好一斤半。
人群里立刻有人起哄,“秋兰,你这眼神准得很啊,一斤半都能看成一斤二。”
“嘴快不怕,怕没心。”沈若棠一句接一句,语气淡,“你这人有嘴没心,嘴一动,别人的饭碗就碎。你这叫能耐?那是祸嘴。”
何秋兰气得脸通红,“你骂谁呢?”
“我骂理丢的人。嘴能欺负秤一回,心能欺负理一辈子。你这毛病不改,迟早没人跟你做生意。”
人群里有人附和,“沈嫂子说得对,她那嘴一年不消停。”
“上次还骂人家卖豆腐的骗她,后来自己称错了也不道歉。”
何秋兰瞪着眼,吭哧半天没挤出一句话,最后扔下豆角袋,“谁稀罕你们这些破菜!”转身走人。
赵茹安忍笑忍得肩膀抖,“妈,您这话也太损了。”
“损?这叫让她记事。嘴坏不是病,惯嘴才是。你不拦她一次,她下回还敢嚷。”
“那要真改得了,她这人不早安分了?”
“改不改不在嘴,在理。理要在,嘴就会闭。你看人得看他愿不愿意听理,不愿意听的,就别搭理。”
赵茹安抿嘴笑,“妈,您这法子真省气。”
“省气才有命。你天天跟有嘴没心的人扯,迟早得气出病。”
她一手拎着豆腐,一手拍了拍女儿的肩,“记着,理直的人不吵,心正的人不躲。别怕别人嘴大,能嚷的多半是理虚的。”
回到家,沈若棠把豆腐放下,顺手拿毛巾擦了擦手。赵茹安还在笑,“妈,您那句‘盐多嘴咸’我得记下来,太绝了。”
“记着也没用,得会用。”
“咋用?”
“遇见那种满嘴跑火车的,你就笑,不争不吵。她越嚷你越稳,最后谁没理一眼就看出来。”
傍晚的街上,风刮得人眼都睁不开。赵茹安抱着买回来的布,袖口被风掀起半截,手冻得通红。
沈若棠正给邻居送完菜回来,一看她那样子,皱眉,“咋又去街那头?那边摊子乱,瞎跑啥。”
“不是乱,是便宜,裁布那家打折,我看着划算。”
沈若棠没说话,先把布接过来,掂了掂分量,手指一抹,布边上都是毛线头。她抬头,语气淡淡的,“你这叫便宜?一尺布能掉半尺毛。”
赵茹安讪讪笑,“妈,我还想着能省两块钱。”
“省两块?你这布用一次就散,你以为钱省了,其实亏得更多。人要是眼里只盯着便宜,迟早得被便宜坑。”
赵茹安撇嘴,“妈,您这人就是太小心。”
“我不是小心,是心疼。
吃过亏的人才知道,省小的容易,守大的难。”
她把布叠起来,递回去,“拿去换。说不好听的,买东西就跟做人一样,要脸。要便宜不要脸的人,商家看一眼就知道能骗。”
赵茹安笑,“妈,您还讲脸?”
“当然讲。你记着——要脸的人,才有命。
不要脸的,看似吃得开,其实走哪都没人搭理。”
赵茹安一听笑出声,“妈,您这话太狠。”
“狠有啥?脸都不要了,还指望别人给你留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