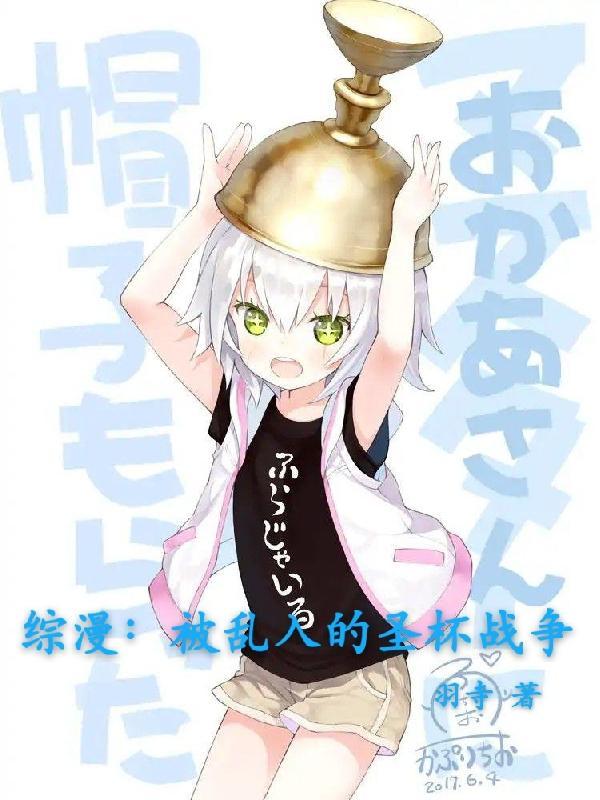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三国:玄行天下 > 第175章 九重诏下战云翻(第4页)
第175章 九重诏下战云翻(第4页)
张宁策马上前,与他并辔而立。她今日未着女装,而是一身特制的鱼鳞细甲,外罩深青战袍,长束成高马尾,以铜环固定。腰间佩一长一短两剑,剑鞘古朴。那张原本清丽的脸庞,因这身戎装平添了七分英气,三分肃杀。
“各部皆已就位。”她的声音很稳,目光扫过眼前无边无际的军阵,“前军五万,麹义统领,已于卯时先行。中军十万,诸将皆在旗下待命。后军五万及全部辎重,由国渊、满宠调度,已从长安陆续运。”
简宇闻言,微微颔,目光却望向北方。
那里,是黄河,是冀州,是袁绍。
十年了。
从初平元年逃离雒阳,到如今坐镇长安,总揽朝政,整整十年。这十年里,他镇豫州,收吕布,灭董卓,平李郭,纳白波,平西凉,定关中,纳刘备,降曹操……一步步,走到了今天。
而袁绍,始终是北边那座绕不过去的大山。
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坐拥冀州,带甲十数万。若不是此人优柔寡断,内部不和,早在三年前,就该有一场决战了。
不过现在也好。
等他收拾完公孙瓒,师老兵疲,正是可乘之机。
“阿宁。”简宇忽然开口。
“兄长。”
“你说,袁本初此刻在做什么?”
张宁略一沉吟:“应在易京城下,督促攻城。或是……正在帐中,摔简骂诏。”
简宇笑了,那笑意很淡,却带着冰冷的锐意:“他会摔的。我太了解他了——外表宽宏,内里狭隘;看似果决,实多疑忌。那道诏书,每一字都戳在他的痛处。董卓之乱,拥立刘虞……这些旧账翻出来,足够他气得三日睡不着觉。”
“所以兄长才让兰平,在天子耳边说了几个月?”张宁问。
“虽然只有几个月,但是也够了。”简宇淡淡道,“有些话,说一遍不信,说十遍将信将疑,说上一百遍……就成了真理。刘协恨董卓入骨,只要让他相信,董卓是袁绍引来的,就够了。”
他顿了顿,补充道:“何况,这本就是事实。”
晨风渐大,吹得大旗猎猎作响。远处传来号角声,悠长而苍凉,那是前军开拔的信号。
“时辰到了。”张宁道。
简宇点头,最后看了一眼身后的长安城。城墙巍峨,未央宫的殿顶在朝阳下闪着金光。这座他经营多年的城池,此刻正在晨光中苏醒,市井的喧嚣隐隐传来,炊烟袅袅升起。
太平景象。
但这太平,是用血与火换来的。要守住这太平,需要更多的血与火。
“出。”
两个字,平静,却重如千钧。
简宇一抖缰绳,踏雪长嘶一声,人立而起,随即如黑色闪电般冲过灞桥。猩红斗篷在身后拉成一道血色的轨迹。
“丞相出征——!”
传令官的高喝声层层传递。战鼓擂响,号角齐鸣。二十万大军,如同沉睡的巨兽苏醒,开始缓缓向北蠕动。
脚步声、马蹄声、车轮声,混成一片沉闷的轰鸣,震得大地微微颤抖。尘土扬起,遮天蔽日,连初升的太阳都变得朦胧。
中军大旗下,众将簇拥着简宇,向北而行。
赵云在左,银甲白袍,坐下照夜玉狮子,手持龙胆亮银枪。他面容俊朗,神色平静,但那双眼睛不时扫视四周,保持着绝对的警惕。夏侯轻衣、马云禄两女在他的身后,手中剑枪显露寒芒,胯下宝马也都是上品,两女就这样跟在赵云身后,为他保驾护航。
而马在右,金甲红披,坐下里飞沙,虎头湛金枪横在马鞍上。这位西凉锦马,嘴角噙着一丝桀骜的笑意,目光灼灼,满是跃跃欲试的战意。
黄忠、刘赪在后,一老一少,皆背强弓。典韦、许褚如同两尊铁塔,一左一右护卫在中军两侧。张合、徐荣、乐进、李典等将,各统本部,军容严整。
孙策也在其中。他今日未着惯常的银甲,而是一身简宇赏赐的玄甲,坐下黄骠马,手提霸王枪。这位小霸王努力克制着兴奋,试图做出沉稳的模样,但眼中闪烁的光芒出卖了他。
贾诩、刘晔两位谋士,乘车跟在简宇侧后。贾诩闭目养神,仿佛眼前千军万马与他无关。刘晔则不断翻阅着手中的文牍,时而抬头观察天色,计算着行程。
大军如洪流,向北席卷。
这一去,便是血与火的征程。
几乎是同一日,午时,兖州,鄄城。
州牧府前的校场上,三万兖州军已集结完毕。这些士兵大多身着皮甲,持长枪盾牌,队列整齐,肃穆无声。春日的阳光有些刺眼,照在枪尖上,反射出冰冷的寒光。
高台上,简雪一身白衣,外罩轻甲。
她没有像寻常将领那样顶盔贯甲,只是简单地将长束起,用一根桃木簪固定。腰间佩剑,剑鞘古朴无华,没有任何装饰。山风吹过,吹起她的衣袂和丝,让她看起来不像统兵大将,倒像云游四方的隐士。
但当她抬眼看向台下三万将士时,那股平静目光中透出的威仪,让最桀骜的军官也低下头去。
“诸位。”
简雪开口,声音清越,不高,却清晰地传到校场每个角落。
“我兄长已率大军北上,讨伐逆臣袁绍。我等奉命,自兖州出兵,攻冀州东南。此战,不为私仇,不为功名,只为——”
她顿了顿,目光扫过台下那一张张或年轻、或沧桑的脸:
“只为早日结束这乱世,还天下一个太平。”
台下鸦雀无声。所有士兵都屏息凝神,看着她。
“我知道,你们中许多人,家中还有父母妻儿。”简雪的声音柔和下来,那柔和中有一种悲悯,“我知道,你们不愿打仗,不愿流血。但有些仗,不得不打。有些敌人,不得不除。”
她抬起手,指向东北方向:“袁绍不除,河北不宁。河北不宁,天下难安。今日我们在此流血,是为了明日我们的子孙,不必再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