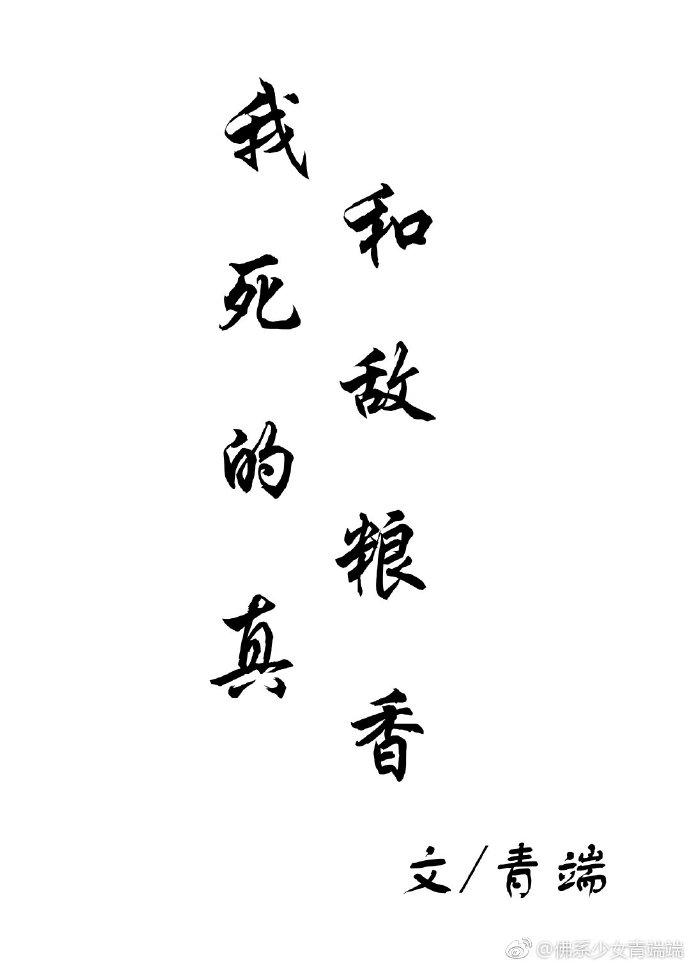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锦凰深宫谋 > 第561章 药炉火起与暗室谜团(第1页)
第561章 药炉火起与暗室谜团(第1页)
乾清宫暖阁,翌日清晨。
晨曦微露,透过窗棂洒入暖阁,驱散了些许夜的寒凉,却驱不散弥漫在空气中的凝重。萧景琰身着素色常服,披着玄色大氅,靠坐在临窗的暖榻上。他脸色依旧苍白,但眼神锐利清明,仿佛昨夜与楚怀远的深谈和那枚锈簪带来的震撼,反而激起了他骨子里深藏的斗志与韧性。内侍刚撤下早膳的碗碟,只余一盏清茶在他手边氤氲着热气。
楚怀远和墨云舟肃立在下,两人眼下都带着淡淡的青影,显然一夜未眠。中间的小几上,并排放着两个锦盒,一个敞开着,露出里面金灿灿的蛇蜕;另一个紧闭,里面是那枚神秘的锈簪以及沈清辞留下的玉簪。
“陛下,”楚怀远率先开口,声音带着熬夜后的沙哑,却异常郑重,“金鳞蛇蜕已连夜以古法初步炮制,药性已激出七成。今日午时之前,配合老朽早已备下的‘七星续脉散’、‘百年血参精华’以及几味固本培元的珍稀药材,便可开炉炼制‘九转还元丹’。此丹专为涤荡邪气侵染、弥补先天元气耗损、稳固惊散神魂而设,最是契合小皇子殿下如今的状况。只是……”
他顿了顿,目光瞥向那个紧闭的锦盒,眉头深锁:“只是这枚锈簪……昨夜老朽与云舟反复查验,甚至刮下微量锈屑,以多种药液测试,现其金属基底确非中原常见之物,其中混有数种南疆特有的稀有矿物,且冶炼手法极为古拙。以锈蚀程度和金属成分变化推算,其年代……恐怕至少在三百年以上,甚至可能更为久远。”
三百年以上!这个结论让暖阁内侍立的凌云和刚刚进来的萧景禹都心头一震。
墨云舟补充道:“臣与祖父仔细比对了锈簪与玉簪的雕刻纹路,特别是并蒂莲瓣的卷曲弧度、花心处几乎微不可察的螺旋纹,几乎分毫不差。可以断定,这两枚簪子出自同一原始模具或设计图样。玉簪传承有序,乃楚家嫡系信物。而这枚锈蚀的金属簪……若真是楚家祖上之物,为何会流落南疆数百年?楚家南迁的记载模糊,难道在更早之前,楚家便与南疆有极深渊源,甚至可能……存在南北分支?”
萧景琰端起茶盏,抿了一口,温热的茶水滑入喉中,带来一丝暖意,也让他思绪更为清晰。他放下茶盏,目光扫过众人:“锈簪年代久远,与楚家祖传玉簪同源,却又流落南疆。贤太妃背后之人,不惜暴露宫中暗桩也要拦截晚莹,阻止此物流入宫中……这几件事串联起来,答案似乎呼之欲出,却又隔着一层浓雾。”
他看向萧景禹:“三皇叔,翰林院和史馆那边,可有收获?”
萧景禹上前一步,递上一份誊抄的纸卷,面色凝重:“陛下,臣查阅了大量前朝及本朝初年的档案、地方志、氏族录,关于‘楚’姓南迁的记载确实寥寥,且多语焉不详。但在一本前朝野史残卷《南疆异闻录》的夹页中,现了一段被虫蛀蚀大半的记述,提及约莫三百五十年前,中原曾有一医术精湛、尤擅解毒祛邪的楚姓家族,因卷入一场宫廷秘案,部分族人南逃避祸,深入苗疆,后不知所踪。而本朝太医院最早的一批医官名录里,恰好有一位楚姓御医,记载其为‘南地归化,医术卓绝’,时间上……大致吻合。”
三百五十年!与锈簪的推断年代竟如此接近!
楚怀远呼吸一滞,猛地抬头:“南地归化……难道我楚家京中这一支,便是当年南迁族人中,后来又北归中原的那一部分?而那枚锈簪……属于留在南疆、或者因故遗落在南疆的另一支?”
“极有可能。”萧景琰缓缓点头,眼神深邃,“若真存在南疆分支,且与京中楚家血脉同源,那么某些针对楚家血脉的阴毒术法,便有了更合理的解释——他们知晓这血脉中可能存在的某种共性或弱点。清辞身上的‘子阵’,或许正是基于这种古老的、可能源自南疆分支的秘术知识。”
这个推断让所有人背脊凉。如果敌人不仅知晓楚家隐秘的南疆渊源,甚至可能本身就与那失落的分支有关,或是得到了其传承……那这场跨越了数百年的阴谋,其根源之深、牵连之广,简直骇人听闻。
“陛下,”凌云沉声道,“孙有德还押在地牢,昨夜用了些手段,他精神已近崩溃,或许能挖出更多关于贤太妃背后之人的线索。是否……”
萧景琰目光一凛:“朕亲自去问他。”
“陛下,地牢阴寒,您的伤势……”萧景禹立刻劝阻。
“无妨。”萧景琰摆手,撑着榻沿缓缓站起,身形虽仍有些单薄,却挺直如松,“有些话,朕亲自问,他才知道该说什么。更有些事,朕需亲眼看看他的反应。楚老,云舟,炼丹之事就全权托付二位,务必确保万无一失。三皇叔随朕同去。凌云,前头带路。”
他的语气不容置疑,带着久违的帝王威严。楚怀远和墨云舟知劝不住,只得躬身应诺,忧心忡忡地看着萧景琰在萧景禹和凌云的陪同下,步出暖阁。
禁军地牢,审讯室。
这里比关押孙有德的牢房更深入地下,阴冷潮湿的气息几乎凝成水珠挂在石壁上。火把的光跳跃不定,将人的影子拉得扭曲怪异。孙有德被从牢房提来,绑在审讯室中央的木桩上,几日折磨下来,他早已形销骨立,眼神涣散,如同惊弓之鸟。
当萧景琰的身影出现在门口,在火把光芒映照下缓缓走入时,孙有德浑浊的眼睛里骤然爆出极致的恐惧,身体不受控制地剧烈颤抖起来,喉咙里出“嗬嗬”的抽气声。
萧景琰并未走近,只是在一张摆放着刑具的案几后坐下,萧景禹和凌云分立两侧。他目光平静地落在孙有德脸上,没有说话,只是那样看着。
无形的压力却比任何酷刑更让孙有德崩溃。他涕泪横流,嘶声哀求:“陛下!陛下饶命!罪臣知错了!罪臣什么都招!是贤太妃!是钱嬷嬷!她们逼我的!”
“她们如何逼你?”萧景琰开口,声音不高,却在地牢中清晰回荡,“详细说来。何时,何地,钱嬷嬷如何传话,原话是什么,一字不许错漏。”
孙有德如同抓住救命稻草,语极快地回忆:“是……是上月廿七,夜里戌时三刻左右,罪臣刚下值,在……在宫外东华门附近一家叫‘悦来’的小酒馆后巷,钱嬷嬷等在那里。她说……说太妃知道罪臣老家父母染病,兄长在衙门当差出了点纰漏,急需银钱打点。只要罪臣帮她办一件小事,就给我三千两……不不,后来又说五千两!还保证我兄长无事,我儿子明年能进国子监读书!”
“她要你办何事?”萧景琰追问。
“她说……说安宁郡主不日将从南边回京,身带紧要之物。让我在郡主回京当日,设法调班到西城门值守,务必拦住郡主,不能让她立刻入宫。最好……最好能探明郡主带了什么特别的东西回来,尤其是……像是旧物、古物一类……”孙有德喘着粗气,“钱嬷嬷还说,这是太妃一位‘故交’所托,此事办成,太妃和那位‘故交’都不会亏待我。若办不成……我全家老小,都别想安生!”
“故交?”萧景琰眼神微眯,“钱嬷嬷可曾提过这位‘故交’姓甚名谁?有何特征?”
孙有德拼命摇头:“没……没有!钱嬷嬷口风很紧,只说是一位连太妃都敬重的人物,在宫里宫外都很有办法。哦……对了!她好像无意间提过一句,说那位‘故交’对南边的老物件特别感兴趣,尤其是……跟医术、古方有关的……”
南边的老物件?医术古方?这指向性已然十分明显!
萧景琰与萧景禹交换了一个眼神。
“钱嬷嬷还说过什么?关于太妃,或者关于楚家?”萧景琰继续问,语气依旧平稳。
孙有德努力回忆,因恐惧而混沌的脑子拼命转动:“楚家……钱嬷嬷好像……好像有一次抱怨,说太妃这些年日子清苦,都怪当年……当年站错了队,没跟着‘那位’一起……具体没说清。还说过……说楚家风光不了几天了,他们的根儿早就烂了什么的……都是醉话,罪臣当时没敢多听……”
根儿早就烂了?萧景琰心中一沉。这恐怕不仅仅是指楚家当年的冤案,更可能暗指楚家那隐秘的南疆渊源,甚至是血脉中的“问题”!
“孙有德,”萧景琰身体微微前倾,目光如炬,直射孙有德眼底,“朕再问你最后一次。除了贤太妃和钱嬷嬷,你还知道宫中或朝中,有谁可能与这件事有关?谁对楚家,尤其是对楚家祖上之事,格外‘感兴趣’?想清楚再答,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孙有德浑身一颤,瞳孔因极度恐惧而放大。他嘴唇哆嗦着,似乎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求生欲压倒了一切,他嘶声道:“陛下!罪臣……罪臣不敢隐瞒!有一次……钱嬷嬷给罪臣银票时,装银票的封套不小心掉出来一角,上面……上面好像有个小小的、红色的印记,像是……像是个特殊的印章,但罪臣没看清具体样子!还有……钱嬷嬷有一次漏嘴,说‘那位’身边有个老仆,手腕内侧有个铜钱大小的红色胎记,很像……很像一朵梅花!”
红色印记?梅花状胎记的老仆?
萧景琰看向凌云。凌云立刻会意,低声道:“末将会立刻暗中排查宫中所有年龄较大的太监、嬷嬷,尤其是曾在各太妃、太嫔宫中伺候过的,以及可能出宫荣养的老人,查其手腕是否有此类胎记。至于那红色印记,需细细描画下来,暗中查访。”
萧景琰点了点头,知道从孙有德这里能挖出的线索大概也就这些了。他缓缓站起身,不再看瘫软如泥的孙有德,对凌云道:“此人暂且留命,严加看管。所有供词,详细记录。”
“末将领命!”
走出阴森的地牢,重见天光,萧景琰微微眯了眯眼。深秋的阳光带着暖意,却照不进他心底的寒潭。贤太妃背后的“故交”,对楚家祖物感兴趣,身边有手腕带梅花胎记的老仆……这些碎片般的线索,正一点点拼凑出一个模糊却更加阴森的影子。
“陛下,接下来如何?”萧景禹低声问。
“回宫。等楚老他们炼丹的消息。”萧景琰声音平静,“同时,按凌云查到的线索,顺藤摸瓜。朕倒要看看,这位藏在贤太妃身后的‘故交’,到底是何方神圣。”
安宁郡主府,内院书房。
楚晚莹端坐在书案后,手中拿着一卷医书,目光却并未落在字上。春桃在一旁轻轻研墨,主仆二人都保持着一种外松内紧的戒备状态。府外的监视并未撤去,甚至更加隐蔽,但昨日深夜,春桃已通过聋哑顾伯,将一封密信成功送了出去。只是不知是否抵达,更不知宫中反应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