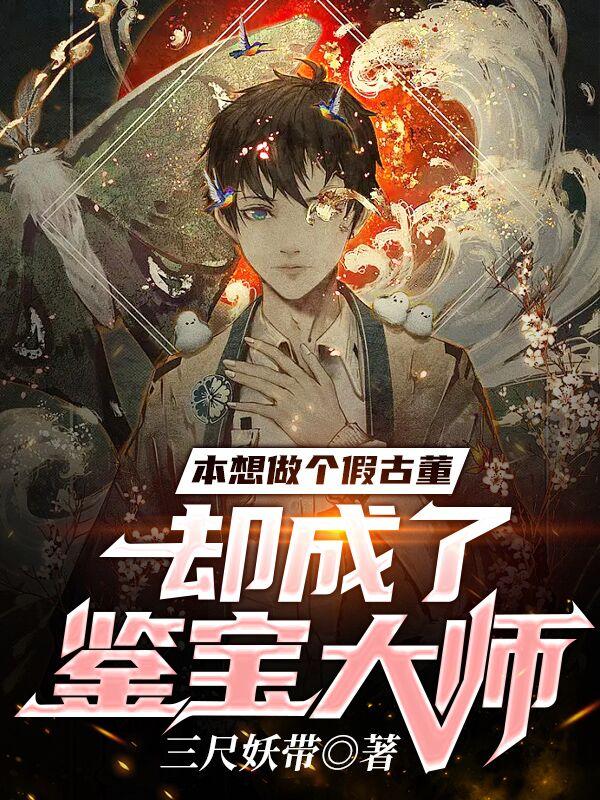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嫡明 > 第401章 臣请乞骸骨(第3页)
第401章 臣请乞骸骨(第3页)
眼看就到正午了,四月的太阳已经有点毒辣,三位阁老都是额头见汗。
三人心中气闷,好在涵养一个比一个好,都是神色平静。他们每次乾清门召对,哪次不是等上好一会儿?
他们凝神倾耳的静听,隐隐听到殿中传来马吊的哗啦声,似乎皇上在打牌?
这都时候了,皇上还有心思博戏!
此时乾清宫内,皇帝、张鲸、高寀、高淮四人正在打马吊。宗钦侍立在皇帝身边,给皇帝烧福寿膏。
打完两圈,皇帝的心情更好了些。宗钦说道:“启禀爷爷,三个阁老在外面等着呢。”
皇帝如梦初醒一般,“怎么不早提醒朕?更衣,出殿。”
出来这才依依不舍的舍了牌局,懒洋洋的站起来,被内侍伺候着更衣,接着出殿升座。
张鲸等太监也跟着一起出来,分立两边。
三个阁老望眼欲穿,终于等到皇帝出现,立刻下拜跪迎道:“臣等叩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身躯肥胖的万历爷被扶着上了御座,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三位辅臣,目中再次现出怒意。
他没有立刻喊平身,而是静静的看着几人,故意让三人多跪一会儿。
三人跪在地上,皇帝不喊平身,他们也不敢起来,只能老老实实跪着。
这其实是皇帝失礼。
足足过了十来个呼吸的工夫,皇帝才语气幽冷的说道:“三位先生平身吧。”
“谢陛下!”王锡爵等三人这才忍气吞声的起身。
堂堂内阁大臣,朝廷脸面所在,礼仪上居然被皇帝故意折辱,当真令人心寒。
“王先生。”万历先看向辅,“他们逼宫的逼宫,罢课的罢课,罢朝的罢朝,辞官的辞官,大明朝还有一点体统吗?肇事者是何肺腑?王先生何以教朕?”
万历开门见山,直接就是问罪。
王锡爵波澜不惊的说道:“今日之事,闹得沸沸扬扬,以至于惊扰圣上,臣等都有不可推卸之责。不过,凡事一体两面,有弊有利。臣等既要向陛下请罪,也要恭贺陛下。”
“哦?”万历冷笑,“午门出了这么大的事,八百官员、万余士人静坐叩阙,还死了好几十人,停尸示威。皇明开国以来,未有今日之祸。王先生居然还要恭贺朕?”
“的确该恭贺陛下。”王锡爵神色认真的说道,“所谓国有诤臣,必然天子圣明。海瑞以八十高龄,率领三千士子入京请愿,若非圣主当国,正气浩然,何能至此乎?安知不是盛世之气象?”
“国家养士二百余年,春风化雨,教化万方,是以四海之内,仁人志士层出不穷。普天之下,君子贤才比比皆是。此乃大明气运之所钟,天命之所象。若非如此,岂有成千上万热血男儿,不远千里入京请愿,视国事为己任?相比万马齐喑、无动于衷,这难道不是可喜可贺么?”
万历闻言,顿时无言以对。他知道对方这是在狡辩,可他偏偏无法反驳。论起耍嘴皮子,他哪里比得上这些经验丰富的文臣?
可他不用反驳,因为会有人替他反驳。
果然张鲸冷声道:“王阁老此言差矣!读书人未必就是君子,道貌岸然、沽名钓誉的伪君子更是多如牛毛、泛滥成灾。眼下京中就数不胜数。他们惯会假公济私,哪里真会忠君爱国?”
他抬手一指外面,“眼下午门那些静坐叩阙之人,其心不可问也!和叛军相比,他们无非就是没有兵器罢了!若教他们有兵器,只怕早就杀入紫禁城!”
“哼哼,你说他们是入京请愿的士子,那么为何要秘密联络信王?为何联络手握兵权的京营将领?如果这也只是请愿,那么有朝一日有人起兵谋反,也能说是请愿了。阁老颠倒黑白,包庇纵容,企图大事化小,避重就轻,莫非就是幕后主使?还是说,信王给了你们什么承诺?”
太监和文臣,同样都擅长吵架,但方式却是不同。
文臣善于吵架,本质上还是辩论,无非是读书读的多,知道很多书中的大道理,说起话来引经据典,无可辩驳。即便是狡辩,也仍然在讲道理。
所以文臣吵架,往往学问越多就越厉害。
太监就不同了。太监吵架不讲那么多大道理,而是不可理喻的无中生有、歪曲事实、指鹿为马、栽赃陷害,底线远不如文臣,与其说是吵架,不如说是诬蔑诽谤。
王锡爵气的胡子都翘了起来,冷冷看着张鲸道:“张公乃司礼监掌印,内相之,也是国家宰相,行事为何如此罔顾法度公理?”
“明人不说暗话,你说他们暗通信王和京营将领,无非是伪造罪证、栽赃陷害而已,然而何以服天下?圣天子神目如电,你又如何能蒙蔽圣聪?难道熟读圣贤书的天下士人,都会相信这些伪造的罪证?”
张鲸笑道:“正是因为很难令人信服,所以他们一旦谋逆,就能收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之奇效,符合兵法诡道也。没人相信书生能造反,反而成了他们谋反的机会。世事无绝对啊,王先生都没有看到罪证,就一口咬定罪证属于伪造,行事如此武断臆测,究竟是何居心?”
张位冷哼一声,“辅是何居心,陛下知,太后知,百官知,天知地知,天下人皆知!张公知与不知,我等从不在意。就算你说我等是谋反,那也是你自己的事,与我等何干?”
王锡爵脱下官帽,再次跪下道:
“陛下,老臣身为辅,难逃其责。老臣今日面君,也不是和内相争辩斗嘴。而是病退请辞,乞骸骨也!”
沈一贯和张位也一起免冠再拜,异口同声的说道:
“士子入京请愿之事,酿成此变,内阁责无旁贷,臣引咎辞职,请乞骸骨!”
胡搅蛮缠是吧?
好,我们不干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