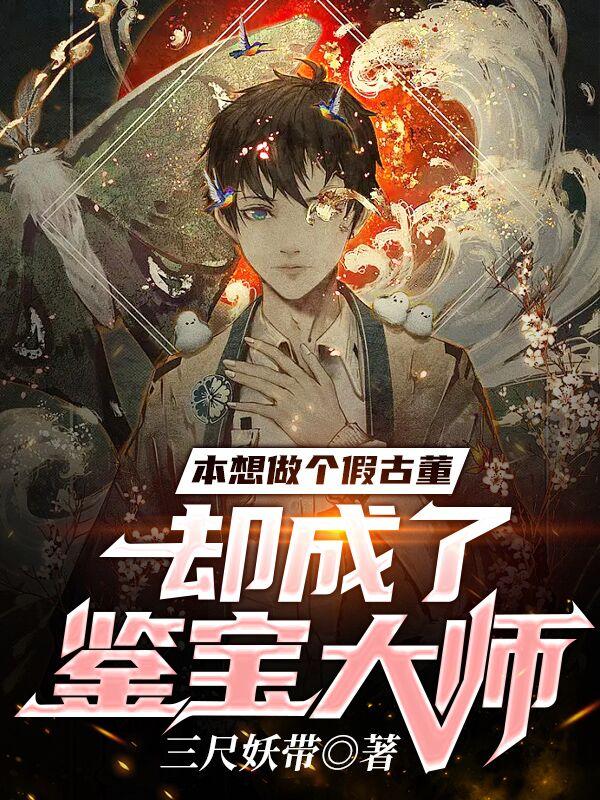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嫡明 > 第401章 臣请乞骸骨(第2页)
第401章 臣请乞骸骨(第2页)
既不能让大家太失望,也不能让君父太为难。
谁知王锡爵等人还没有等到王驾,却等到了前来传达口谕的御马监掌印太监,宗钦。
“各位相公。”宗钦笑眯眯的说道,“陛下因为身子欠安,临时不能驾临文华殿了,已经半途折返乾清宫。陛下口谕,传三位阁老乾清门陛见。其他相公,就不见了。”
什么?众人顿时郁闷至极。这不是儿戏么?上谕让他们来文华殿议事,怎么皇上又变卦了?
还以为皇上开始转性,来文华殿议事就是一个好兆头,谁知半途又回乾清宫了!
乾清宫距离文华殿不到一里地,御辇半刻钟就能到,可皇上都不愿意来!
这像话么?
阁臣和九卿都是脸色阴沉,心中失望。
王锡爵只能说道:“请宗公公回禀陛下,臣等三人随后即到,烦陛下稍后。”
等到宗钦离开,左都御史李世达先怒道:“陛下这是言而无信!了上谕说驾临文华殿议事,召集我等前来,结果又折回了后宫,只见阁臣!”
吏部尚书孙丕扬冷声道:“陛下怠政一至于此,越来越儿戏国事了。海公临终前的担忧,怕是都会应验。君父如此任性,我等身为臣子,如何自处?”
“如何自处?”礼部尚书罗万化冷笑一声,“无非是辞官罢了。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王锡爵叹息一声,说道:“诸位先去午门维持秩序吧,让百官和士子们稍安勿躁。我等三人自去乾清门。诸位放心,内阁一定帮陛下拿出一个章程,横竖要有个交代。”
孙丕扬浓眉一扬,“三位阁老,见了陛下不会一味迁就吧?元辅,你可一定要坚守底线。”
罗万化也道:“是啊三位阁老,若是陛下不愿让步,我等的底线也万不可失,海公的谥号,还有入京请愿的定性,就是底线。”
其他人也一起点头。
没错,给入京请愿一个正面的定性,给海瑞一个好的谥号,就是群臣的底线。底线守住了,说明局势大体可控。若是这个底线守不住,那么朝政就会彻底失衡,宦官集团可能会真正把持朝政,重演东汉晚唐故事。
张位说道:“今日,张某就算殒命乾清门,也绝对不会让陛下任性。不过一死而已!皇明二百多年,被杖毙的谏臣数不胜数,多我一人何妨!”
王锡爵白须飘飘的沉声道:“此事必然要有人出面负责,我是辅,舍我其谁?事情闹到这一步?总不能让君父下罪己诏吧?可我辞官前,拼却这身朽骨残躯,也要妥善解决此事,还请诸位放心。”
他知道,自己这个辅已经当到头了。前次王师在高丽大败,是次辅赵志皋出面背锅请辞,现如今赵志皋已经致仕回乡。今日甲寅之变,轮到他这个辅出来担责了。
总不能让陛下担责。
平时,文臣们绝非铁板一块,相互之间党同伐异、排挤异己是常有之事。可是此时此刻,绝大多数文臣都不计前嫌的团结起来,凝聚一心。
他们清楚,这次事件已经不仅仅关系到国本之争了,更是关系社稷危亡、大明国运。
一旦皇帝随心所欲,宦官势力滔天,不但士人会丧失朝堂权柄,中央朝廷也会和地方对抗,天下大乱就难以避免了。
孙丕扬等九卿一起肃然拱手道:“大事就拜托内阁了。我等就在外面静候佳音。”
三位阁臣正正衣冠,并排出了文华殿,往乾清门而去。
过了外朝的徽音门,用腰牌通过景运门,就是后宫区了。
三位阁老进入后宫,看见巍峨的乾清宫,不禁很是感慨。
大明开国以来,大臣极少能进入后宫区。皇帝上朝议政,也都是出了乾清宫到前朝的三大殿,或者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
可是当今皇帝,已经好几年不来前朝,就算偶尔议事就也是召大臣进入后宫,到乾清门召对。
就连王锡爵等内阁大臣,往往也是几个月才能见到皇帝一面。九卿大多一年也见不到天颜。
九卿以下的大臣,除了极少数人之外,已经几年没见过皇帝了。以至于入仕时间不长的朝臣,甚至都不认识皇帝,不知道皇帝长什么样子。
三人心事重重的穿过乾清门广场,来到乾清门的月台下。月台之上,就是天子寝宫乾清宫了。
三人拾阶而上,来到月台西侧,向东而立。
他们并没有进入乾清宫。因为皇帝召见他们,向来就是在这乾清门的月台,而不是在宫殿之中。他们为官多年,一次也没有进入乾清宫中。
乾清门内外侍卫肃立,仪仗森严。乾清门外的御座已经陈设好了,两个宫女手持仪扇肃立。
可是御座上却是空空如也,没有看到皇帝的身影。
皇帝还没出来。
那便等着吧。反正皇上就在里面,横竖跑不了。
“元辅,张先生,沈先生。”宗钦出来说道,“请在此候着吧,爷爷稍后就出殿升座了。”
三人点点头,当下肃立月台,静候天子升座。
然后三个位高权重的内阁大臣,等了足足两刻钟,皇帝也没有出殿升座。
三人都是老人,站的都有点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