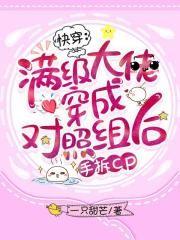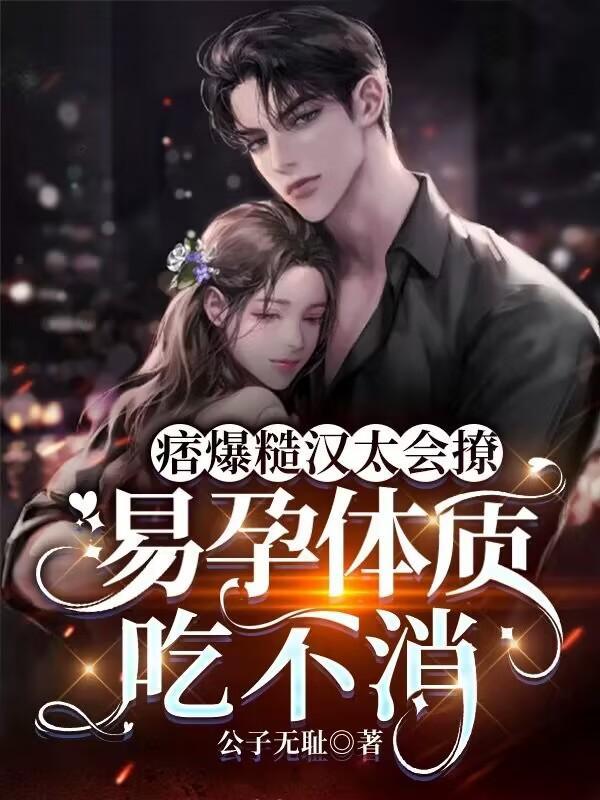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嫡明 > 第377章 朕命诸卿投降大明(第2页)
第377章 朕命诸卿投降大明(第2页)
可惜多少大才被科举蹉跎,白了少年头啊。对秀才和举人来说,经由幕僚辗转出仕也是一条出路。
果然,孙承宗朗声道:“先生折节下交,稚绳惶恐。我二人科场蹭蹬,功名未就,然闻倭寇肆虐,社稷有事,自问不敢避世,特来投效帐下,愿效犬马之劳,尽书生绵薄之力。”
高攀龙神色有点赧然,“晚生三次会试,至今未第,已经不能再考。终身止步孝廉,空有报国之心,惭愧,惭愧。”
按照如今的科举规则,举人一般连考三次不中,就没了考试资格。他不知道的是,若非穿越者出现,他早在几年前就考中进士了。
“稚绳兄、存之兄。”朱寅亲手奉上热茶,“功名乃一时之遇,经世济民方是我辈本分。孔圣厄于陈蔡,孟轲困于齐梁,然其道…益彰。”
“二位兄台心怀天下,跋涉万里而来,此等气节担当,远胜于金榜题名矣!”
朱寅神色诚恳,语气也很恳切,“此间无尊卑上下,无须自称晚生,大家兄弟相称最好,有志同道合者,可论道也。朱寅愿闻二位高见,于这乱世之中,治国安邦、经世致用之道,究竟何为根本?”
这当然不是考较。朱寅知道这两位的才情思想,都是当世之英,根本不必考较。他只是想让两人有抒的机会。
高攀龙轻啜一口热茶,温言道:“晚生浅见,窃以为治国之要,在‘正心诚意’。《大学》有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以修身为本。”
“就说这倭寇之祸,究其根由,存之观之,恐在于国朝人心不古,道德陵夷。朝廷若欲攘外,必先安内;欲安内,则必以教化正人心为始。使在上者公忠体国,在野者知礼明义,上下同心,则内忧自弭,外患亦可御也。”
“人心不正,则正气不存,人心思变不思危,自然心怀怯懦,不能制侵凌。”
朱寅听到这句话,差点脱口叫好。高攀龙说的太好了:若是正气不存,便是人心思变而不思危,民众就心怀怯懦。民众心怀怯懦,自然很难抵抗外辱。
“此即内圣方能外王之理。”高攀龙语气平和,目光莹然中流露出对道德重建的执着,“天下若是正气沛然,便是暴君亦不可得逞,贪官亦不可遁形。”
“人心教化,绝非空口白话,泛泛而谈,只要改良朝廷政治,践行公道德政,还以施政清明,就能春风化雨,潜移暗化。”
“善哉,善哉!”朱寅点头赞赏,深以为然,他知道高攀龙的意思。高攀龙是古典民主派,他的这段话不是大而无当,而是带着宪政色彩了。
这是晚明时期在宪政上走的比较远的一位,主张建立限制皇权、广泛参政议政的制度。
高攀龙大胆阐述“天之生民非为君,天之立君以为民”,颠覆“君权神授”,赋予皇帝服务者的职能。宣称:“若君虐民,则民可问天!”
此君历史上,对抗朝廷的法子就是起舆论和公议,用民意来制衡朝廷的胡作非为。
胆子这么大,他当然很难活。终于跳水自杀。
高攀龙个人道德水准很高,真如他诗中说的“心同流水净,身与白云轻”。
孙承宗闻言,放下茶盏,接口道:
“存之兄所言,‘正心诚意’乃为政之基,在下深以为然。然愚以为,时局危殆如累卵,仅凭道德感召,恐缓不济急。”
若说高攀龙更在意思想上的正人心,那么孙承宗更在意现实中的成实务。一个形而上,一个形而下。而两人恰恰为挚友。
他目光炯炯,“管子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治国理政,须明法度、核名实、兴屯田、通漕运、强武备。使民有恒产,兵有饱食,法令严明,赏罚必信。惟此,方能根基稳固,王道施行,外御强敌,内抚黎庶……”
孙承宗的声音沉稳有力,带着一种穿透力,他更关注具体的实际问题的解决。
朱寅听二人各抒己见,眼中毫不掩饰自己的欣赏,点头缓缓道:
“二位兄台所言,或重心性之本,或倡事功之用,看似殊途,实则同归,比如阴阳相济,皆为圣贤大道不可或缺之双翼也。”
他看向高攀龙,高屋建瓴般侃侃说道:
“存之兄忧心道德陵夷,实为洞察根本。无内圣之基,外王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人心不正,则法令愈繁,奸弊愈生。教化之功,润物无声,看似迂缓,实乃长治久安之基石。正人心,厚风俗,使天下归仁,此乃根本大计,在下深以为然。”
他又转向孙承宗,同样肯定道:
“稚绳兄强调实学,实政,更是切中时弊。《尚书》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若民生凋敝,仓廪空虚,武备废弛,纵有尧舜之心,亦难行仁政于天下。非常之时,当行非常之实政。明法度以制奸邪,励殖产以实仓廪,整军备以慑夷狄,此皆外王之筋骨,不可或缺。”
朱寅站起身,一双慧眼目光迥然,语气沉凝而铿锵:“然则,心性与事功,内圣与外王,犹如身与魂,刀与锋,岂可割裂?王子倡‘知行合一’。心性乃事功之魂,事功乃心性之用。”
“无仁心之实政,易流于苛酷,如秦之暴法;无实政之仁心,则易沦为空谈,如魏晋之清议。”
孙承宗和高攀龙向来为友,可也经常争论。朱寅的话他们当然清楚,可孰轻孰重,谁主谁副,他们却又莫衷一是。此时听到朱寅言及此处,知道今日便可了结一桩辩论,都是肃然聆听。
朱寅完全不像个十六岁的少年,句句老气横秋,字字苍音龙钟。他喝了一口茶,继续说道:
“存之兄正心诚意之教,乃铸魂立本。稚绳兄务实求效之策,乃强筋壮骨。二者交融,方能使仁政有根基,实政有灵魂,绝不可偏废,亦不可缓急有别。在下有一句市井俗话概括,便是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孙承宗和高攀龙听到这句话,虽然觉得的确俚俗,可却极其精当,很有大俗而雅之妙。
光听朱寅这番话,就知道稚虎先生的确学识渊博,天生宿慧,大有真知烁见,不输当世大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