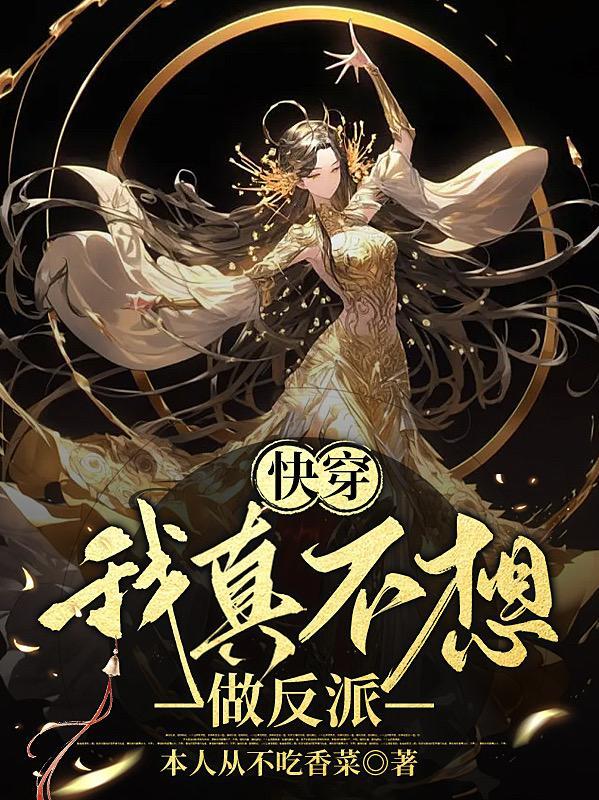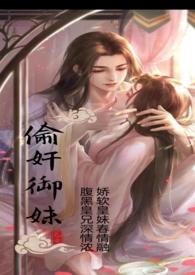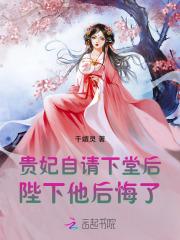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生个孩子姓易,把一大爷钓成翘嘴 > 第36章 出差的主线任务从来不是出差本身(第3页)
第36章 出差的主线任务从来不是出差本身(第3页)
韦东毅停下车,意念微动,车斗里那四百多斤鲜活的海产瞬间消失,整齐地出现在市空间里。
车斗底部,只留下湿漉漉的海草和一点海水,散着淡淡的海腥味。
走到海边。
夜色中的大海深邃而神秘,涛声阵阵,海风带着沁人的凉意吹散了白天的燥热和渔村的腥气。
他找了块礁石坐下,望着黑暗中起伏的海面,听着永不止歇的潮声,连日来的喧嚣和算计仿佛都被这无边的黑暗与涛声吸走了,身心感到一种难得的宁静和放空。
月光洒在海面上,泛起粼粼波光。
他抬起手腕,借着月光看了看表,已经在这里静坐了一个多小时。
该回去了!
他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沙粒。
动汽车,吉普车掉头,沿着来时的土路,朝着远处渔村那几点微弱的光亮驶去。
明天,还有一车“海鲜”要装呢。
吉普车的大灯刺破渔村浓重的夜色,缓缓驶回胡家堡时,村口聚集闲聊的村民们早已站起身,翘以盼。
韦东毅刚停稳车,胡三浪那张被海风和日头刻满皱纹的脸就从人群中挤了出来,带着渔家人特有的热情笑容迎上来。
“韦同志!您可算回来了!住处都收拾妥了,就在我家东屋,床铺都换了干净的被褥!”胡三浪的声音洪亮,带着海腥味的晚风也掩不住他的热忱。
韦东毅连忙道谢,目光扫过围观的村民和几个探头探脑的孩子。
他心念一动,对胡三浪道:“胡支书,麻烦您把村里的小家伙们都叫来吧,我这有点四九城带来的稀罕糖,给孩子们甜甜嘴。”
胡三浪一愣,随即笑得更加开怀,连声应下,转身就吩咐身边的小伙子去挨家喊人。
村子不大,拢共三十来户,大大小小的孩子很快就被聚拢过来,约莫二三十个,大的十来岁,小的还在母亲怀里抱着,小脸被海风吹得红扑扑的。
孩子们怯生生地看着这位城里来的“采购员大官”,眼睛里闪烁着好奇又期待的光。
韦东毅打开吉普车后座,拿出一个用旧报纸包着的纸包,里面是剥掉了彩色糖纸、只剩下白色糯米纸包裹的大白兔奶糖——这是他从市空间特意准备的“土特产”。
他笑着挨个分,无论大小,每人一颗。
奇妙的是,每个孩子接过糖,不管是被父母推着,还是自己懂事,都会用带着浓重乡音或奶声奶气地说一声“谢谢叔叔”。
这淳朴的谢意,让韦东毅心头微暖。
这个小小的插曲,瞬间拉近了韦东毅与渔村人的距离。
刚才还带着几分拘谨的村民们,脸上的笑容变得真诚而放松。
夜色渐深,众人却没了睡意,三三两两坐在村口的石墩、木桩上,借着朦胧的月光和远处大海的涛声闲聊起来。
渔民们绘声绘色地讲述着惊险的出海经历,鱼群、风浪、暗礁,还有那些关于大海的古老传说。
韦东毅则给他们描绘着四九城的红墙绿瓦、宽阔的长安街、巍峨的天安门,以及城里人生活的点滴。
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在这小小的渔村口,借着星光和海风,悄然交汇。
直到夜深露重,胡三浪提醒很晚了,大家才意犹未尽地散去。
躺在胡三浪家东屋的土炕上,身下是铺着厚厚干草、散着独特气息的褥子。
屋外,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清晰可闻,时而低沉如闷雷,时而清脆如碎玉。
这从未有过的枕涛声,让习惯了城市喧嚣的韦东毅一时难以适应。
他在硬实的炕席上辗转反侧,听着窗外海风穿过渔网的低吟,以及远处隐隐约约的犬吠,
思绪纷飞。
直到午夜过后,身体的疲惫才终于压倒了新鲜感带来的兴奋,将他带入并不算安稳的梦乡。
……
清晨七点,天光已经大亮。
韦东毅推门出来,现胡三浪家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几只芦花鸡在悠闲地踱步啄食。
厨房里传来锅碗瓢盆的轻响,胡三浪的老婆正利索地收拾着。
看到韦东毅,这位朴实的渔家妇女脸上露出憨厚的笑容:“韦同志醒了?快洗漱,早饭给你留灶上热着呢。”
韦东毅有些不好意思地答应着,迅完成了洗漱。
等他回到堂屋,桌上已经摆好了一碗热气腾腾的“海鲜粥”——说是粥,更像是棒子面糊糊里混杂着切碎的、不知名的小海贝和咸鱼干丁,散着浓烈的海腥气。
这是渔村清晨最寻常的味道。
“婶子,胡支书这么早就出去了?”韦东毅一边坐下,一边随口问道。
“可不是嘛!”胡三浪老婆一边擦着手一边说,“天蒙蒙亮就跟着船队出海了。近海转转,估摸着九十点钟就能回港。他交代了,你要是闷,可以跟大伙儿去滩涂上赶赶海,捡点小玩意儿玩玩。”
赶海?韦东毅眼睛一亮。
这倒是体验渔村生活的好机会。
他三口两口扒完了那碗风味独特的“海鲜粥”,赶紧回屋拿出了自己的相机。
镜头记录下这个时代最真实的渔家日常,也是他此行的意外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