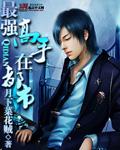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星恋雅望—还好没错过你 > 第75章(第2页)
第75章(第2页)
林晓晓笑着扔给他个线轴,正好砸在他背上。窗外的石榴树结了个红灯笼似的果子,在风里轻轻晃。她拿起刚织好的小马甲,灰色的毛线透着点旧,却暖得像团火。
她知道,这旧毛衣里藏着的,不只是念安的青春,还有周明宇笨拙的补丁;这新棉鞋里装着的,也不只是银线和灯芯绒,还有对那个陌生姑娘的暖,对念安的盼,和那些坐在缝纫机前,听着风扇“嗡嗡”转的午后。
锅里的红烧肉“咕嘟”响,像在唱支暖乎乎的歌。林晓晓把小马甲套在念念的玩偶熊身上,大小正好,熊的圆脑袋顶着灰色的领口,像个偷穿衣服的小老头。周明宇拎着五花肉回来时,她正给棉鞋缝鞋带,红色的布条在她手里绕来绕去,像条小小的红蛇。
“真香,”周明宇凑到厨房门口,“比你妈做的还香。”
“就你嘴甜。”林晓晓笑着把他推出厨房,“去给风扇换个滤网,别吹得满屋子灰。”
风扇换了滤网,吹出来的风带着点清冽,拂过缝纫机上的棉鞋,星星的银线在风里闪。林晓晓看着鞋面上的星星,突然觉得,这针线里缝的哪是布,分明是日子——是念安哭着说“补丁是荣誉勋章”的傻样,是周明宇笨手笨脚扶布料的认真,是那个素未谋面的姑娘,穿上棉鞋时暖起来的脚尖。
这样的日子,真好。
四、针线笸箩里的星辰
寒露的清晨,林晓晓蹲在阁楼的地板上,翻找着个旧木箱。箱子是她结婚时母亲给的,红漆已经掉了大半,锁扣上缠着圈红绳,是当年周明宇非要系的,说“像个同心结”。
“找到了!”她从箱底翻出个蓝布包,解开绳子,里面是半笸箩的旧针线:褪色的绒线、生锈的顶针、还有本泛黄的绣谱,封面上写着“百鸟朝凤”,是她外婆传下来的。
周明宇抱着个旧台灯进来,灯座上画着朵牡丹,颜料已经剥落。“这台灯还能用,”他把台灯放在桌上,插电试了试,暖黄的光洒在布包上,“给念念当床头灯正好,她说怕黑。”
林晓晓没说话,指尖拂过绣谱上的“凤”字,笔锋遒劲,是外婆的笔迹。她想起小时候,外婆总坐在窗边,戴着老花镜,给她绣肚兜,说“女孩子要戴点花,才好看”。那时的阳光也像现在这样,暖融融的,照在外婆的白上,像撒了把碎银。
绣谱里夹着张黑白照片,是外婆年轻时的样子,她穿着件蓝布衫,手里拿着件绣了一半的嫁衣,嘴角的笑像朵盛开的菊。“你看外婆的手艺,”林晓晓把照片递给周明宇,“这凤凰的羽毛,一根是一根,比现在机器绣的强多了。”
周明宇拿起照片,在手里掂了掂:“跟你绣的星星有得一拼。”他突然从箱底翻出个铁皮饼干盒,“这里面是念安小时候的‘宝贝’,你看看有没有能用的。”
盒子里装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断了腿的塑料奥特曼、缺了角的橡皮、还有颗用线串起来的纽扣——是念安第一次掉的乳牙,林晓晓用红线串起来,说“这样能长颗整齐的新牙”。
“这纽扣能当绣绷上的珠子,”林晓晓把纽扣串挂在笸箩的把手上,“给念念绣个香囊,正好当装饰。”她想起念安掉牙那天,哭着说“牙没了,不能啃排骨了”,周明宇抱着他去买了根冰棍,说“冰的不硌牙”。
阁楼的天窗开着,风灌进来,吹得绣谱“哗哗”响。林晓晓把绒线绕回轴上,突然现其中一团绿线里,裹着颗小小的玻璃珠,是当年给念念绣虎头鞋时剩下的,说“当老虎的眼睛正好”。
“这珠子亮,”周明宇拿起玻璃珠,对着光看,“像星眠说的那颗参宿四,红通通的。”他突然想起什么,“念安说他们现了颗新的小行星,想叫‘晓晓星’,问你同意不。”
林晓晓的手顿了顿,眼眶有点热。“叫‘念念星’吧,”她说,“那丫头天天盼着有颗星星跟她重名。”她从笸箩里翻出块紫色的绸缎,“给高雅绣个书签,她总说‘书里夹片绣品,翻起来都香’。”
绸缎是当年给周明宇做棉袄剩下的,紫得像深冬的夜空。林晓晓的针在绸缎上游走,银线绣出的星轨渐渐成型,像参宿四的光,穿过六百年的距离,落在布面上。
周明宇蹲在旁边,给她递剪刀,突然指着窗外:“你看,星眠和念念在院子里跳皮筋呢,念念的新鞋还是你上周给她做的。”
林晓晓走到天窗边往下看,星眠穿着件蓝色的连衣裙,念念穿着双粉色的绣花鞋,两人的皮筋在阳光下跳,像条彩色的蛇。高雅站在旁边,手里拿着件刚织好的毛衣,是给宫琰煜的,袖口绣着颗小小的星。
“她们俩,”林晓晓笑着说,“像极了我和你妈年轻时,总爱凑在一起做针线活。”她想起当年和高雅初见面,两人坐在老宅的玉兰树下,她给念安缝书包,高雅给星眠织帽子,宫琰煜和周明宇蹲在旁边,一个削木头,一个修自行车,像两只守着窝的老鸟。
阁楼的风带着点凉,吹得绣谱又“哗哗”响。林晓晓把绣好的书签放在桌上,紫色的绸缎上,银线的星轨闪着光,像把整个宇宙的暖,都绣在了布里。
周明宇端来杯热茶,放在她手边:“下去吧,高雅说要跟你学绣星轨,说‘给宫琰煜的望远镜套个绣套,显得有文化’。”
林晓晓笑着点头,拿起针线笸箩往楼下走。笸箩里的顶针、绒线、绣谱在她怀里轻轻晃,像装着一整个星空的暖。她知道,这针线里藏的哪是布和线,分明是岁月——是外婆坐在窗边的白,是念安哭着说“牙没了”的傻样,是念念盼着有颗“念念星”的期待,是高雅说“绣套显得有文化”的笑。
这样的岁月,真好。
五、布包里的岁月长
冬至的雪下了整整一夜,清晨起来,院子里的葡萄架裹了层白,像盖了床厚厚的棉被。林晓晓坐在炕头,膝盖上摊着块深蓝色的棉布,手里的绣花针穿来穿去,在布面上绣出个圆滚滚的雪人,帽子用的是红色的丝线,像顶小小的圣诞帽。
“又在给念念做棉裤?”周明宇端着盆炭火进来,炭盆里的火炭红通通的,映得他的脸也暖烘烘的。他把炭盆放在炕边,凑过来看,“这雪人的鼻子怎么是三角形的?像块小砖头。”
林晓晓抬手用针尖戳了下他的胳膊:“这叫‘有棱角’,你懂什么。”她把棉布往旁边挪了挪,露出身边的针线笸箩,里面插着十几根针,线轴摆得整整齐齐,最底下压着张泛黄的纸,是她妈画的雪人花样,旁边写着“鼻子要尖,像胡萝卜”。
周明宇也不恼,蹲在炭盆边烤手:“菜园的萝卜冻了,挖出来给你当模型?”他突然想起什么,从柜子里翻出个布包,“你妈寄来的旧物,说让你看看有没有能用的。”
布包里堆着半箱布料:靛蓝的粗布、印着牡丹的缎面、还有块磨得亮的灯芯绒,上面沾着点奶渍——是周明宇小时候穿的罩衣。最底下压着件没缝完的棉袄,领口绣着半只喜鹊,针脚歪歪扭扭的。
“这是我妈当年给我爸绣的,”林晓晓摸着棉袄上的线头,“她说绣到一半生了我,后来总说‘等有空补完’,结果到现在还是个半成品。”
周明宇拿起棉袄,对着炭盆的火光看:“挺好看的,缺只眼睛才特别,像我画的画——小时候老师总说我画的人少只耳朵,说‘这叫抽象’。”
林晓晓被他逗笑了,针差点掉在炕上。她想起刚认识周明宇时,他给她画肖像,把她的辫子画成了两根麻花,还得意地说“像你做的油条”。那时候他总爱往她的针线笸箩里塞些“宝贝”:捡来的彩色玻璃片、磨圆了的鹅卵石,说“能当绣花的花样”。
窗外的雪又开始下了,簌簌的,像撒了把盐。林晓晓的针在布面上游走,红色的丝线绣出的雪人帽子渐渐成型,边缘的绒毛像真的在飘。周明宇蹲在炭盆边,给她递剪刀、穿针线,笨手笨脚地把线穿进针眼,却总把线头留得太长,惹得林晓晓总说“你这是给线留了条尾巴”。
“念念在幼儿园画了幅画,”周明宇突然说,“画的咱们仨在雪地里,她手里举着件棉裤,说‘妈妈做的,有雪人’。”他从口袋里掏出张皱巴巴的画纸,上面的小人脑袋比身子大,棉裤上画满了圆圈,像缀了串小太阳。
林晓晓接过画纸,贴在胸口,眼眶有点热。她想起念安小时候,也总爱画她坐在炕头,说“妈妈的针会跳舞”。现在那孩子长到比她还高了,上周回家,还特意给她带了包苏州的丝线,说“比咱们这儿的亮,绣星星好看”。
“对了,”她想起什么,“高雅说晚上来包饺子,让我给星眠做双棉拖鞋,她总说实验室的空调太凉。”她从笸箩里翻出块灰色的珊瑚绒,“这料子暖,像踩在云朵上,我妈说‘冬天穿珊瑚绒,脚不生冻疮’。”
周明宇拿起珊瑚绒,往脸上蹭了蹭:“是软和,比我穿的袜子强。”他突然跑去院子,抱来盆仙人掌,花盆上贴着张纸条,是念念写的“爸爸养的,别碰”。“你看,”他指着仙人掌,“这刺像不像你绣老虎用的金线?”
林晓晓白了他一眼,手里的针却没停,珊瑚绒上渐渐显出个小小的星轨图案,是高雅说的猎户座,银线在灰布上闪,像真的有星光在流。她突然想起去年冬天,高雅来借顶针,两人坐在炕头,她给星眠缝棉鞋,高雅给宫琰煜补毛衣,周明宇和宫琰煜蹲在炭盆边,一个削木头,一个擦望远镜,斧头落在木头上的“咚咚”声,混着针线穿过布料的“沙沙”声,像支最暖的歌。
傍晚收工时,棉裤的前片绣好了,雪人的红帽子在炭火的光下泛着暖,像朵开在布上的花。林晓晓把棉裤套在念念的玩偶熊身上,大小正好,熊的圆脑袋顶着红帽子,像个偷穿衣服的小胖子。
周明宇端来碗热腾腾的姜汤,里面放了红糖和姜片,暖得像团火。“念念说要带同学来家里堆雪人,”他舀了勺姜汤给她,“说要让同学看看妈妈绣的雪人。”
林晓晓喝着姜汤,甜辣的味道混着布料的气息漫在舌尖。她看着炕头的棉拖鞋半成品,看着布包里的旧棉袄,看着周明宇笨手笨脚添炭火的样子,突然觉得,日子就像这针线笸箩,看着乱哄哄的,其实每根线都有去处——旧的布能拼出新的花样,缺只眼睛的喜鹊藏着老一辈的念想,笨拙的关心裹着最实的暖。
窗外的雪还在下,像给院子盖了层厚厚的糖霜。林晓晓拿起针线,准备给棉拖鞋绣上最后颗星星。她知道,这针脚里藏着的,不只是线和布,还有给星眠的暖,给念念的盼,给周明宇的笑,和那些坐在炕头,听着雪落、针脚沙沙的冬夜。
这样的日子,不慌不忙,像件刚做好的棉裤,暖烘烘的,刚刚好。
![甘愿[校园1V1]](/img/29299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