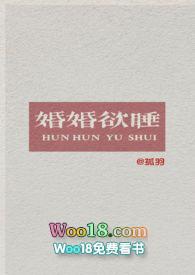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天青之道法自然 > 第4章 鹿鹤养生丸(第2页)
第4章 鹿鹤养生丸(第2页)
说不好听点的呢,那就是矫情,太敏感了倒是常人跟不上他个思维。
说到这里,我严重怀疑这货是不是水瓶就是巨蟹的。这多愁善感的,都快抑郁了。可偏偏生在五月,金牛一个!这到哪说理去?
搭上这奉华宫主事也是个不经常伴驾的,吃不准这官家的脾性。且是把这事当真了也。
却不说是那童贯,便是那黄门公,也不容他多想了去,随便找个新鲜的玩意引了他去。不过晌午,便又能重新点燃他对生命的渴望。
然,文青的病,恐怖就恐怖于此!你不准备吧?他说你轻慢,但是你真的去按他说的准备,他则又瞠目瞪了你,道上一句“合着你们都盼着我死啊!”
这两头堵的,着实的让人受不了。
现在闹成这个样子,便使了性子逐了宫人,闭门不见任何人,这麻烦的饶是一个劲劲的。
这黄门公与那奉华宫主事一路絮絮叨叨的疾行到的那奉华宫门前。却是看了一个傻眼。
见那宫门紧闭,门前哭哭啼啼的跪了一大片!
心道:你们还真实在啊!还他妈的真哭上丧了?
恼的那黄门公除了骂宫人也只能犯愁的挠头,转了圈的推磨。
怎的?进去便是一个抗旨!不进去便是狼心狗肺的冷酷无情,看着皇帝死也不管!
这就是伸头缩头都是一刀!左右都是个死啊!
且在束手无策之时,却见那龟厌搀扶了那怡和道长缓步而来,见黄门公如此便问了一句:
“怎的不进去?”
只这一句且是让那黄门公干张嘴不说话,怎的?无fuck说!
这事吧,说来且是一个麻缠,一时半会说不大个清楚。
但是,说来也太简单,倒是一句话就能说明白。但是他却是一个不敢说。
说什么?怎么说?说我们官家神经病犯了,挨里面憋着给自己办丧事呢。
这话,他倒是敢说?毕竟人还没死呢!敢张嘴就是个大不敬!
这能说明白的不敢说,不能说明白的,又是一个说了白说。
于是乎,便让这老媪一个瞪了眼流口水,生生的一个哑口无言。
那龟厌看了那黄门公张大个嘴,嘴角挂了涎液且是个惊奇。
如此便不再问他,自怀中掏了个帕子与他擦了。刚想收了去,却见上有涎液,又犹豫了一下,将那帕子直接塞到那黄门公手中。遂,扶了那怡和道长推了宫门入内,饶是留的宫外一帮人傻眼。
说话间,两人便进了那奉华宫内,偌大的宫内却是不见个人影。
总算是见到这玄阵了!怡和道长心下叹道。
入眼,倒是一个平常的黑虎白砂的化煞,且是一个咔咔的挠头,倒是想不出,龟厌、唐昀这俩人所言的那般神奇!
见四下无人,那怡和道长便推了自家师弟那关心的手道:
“不用你扶我,分头行事,你我尽快,做完了好跑路!”
这话说的那龟厌一个瞠目,心道:你就怎么不待见这皇帝?
然,心下一轮,便又心道:这冷酷无情无理取闹的死玩意儿,还是离他越远越好!端端的是个难缠的主!
不过,想死我一个!不能够!要死一起去!
想罢,便又攥紧了自家这想要躲清闲的师哥,道了声:
“诶,师哥,还是同去麽!”
却在这俩师兄弟纠缠撕扯个不清爽之时,见白沙空林之中,那孤独白羽黑翅的鹤,呆呆的站了望了他俩,饶是个显眼。
原本这鹤,也是悠哉游哉四处刨食闲逛。
然,见那龟厌两人进来便是鹤眼前一亮,那叫一个热情似火,仰头鹤唳一声,便扇了翅膀一路跳跃而来。且用那长喙在那龟厌身上上下急急的翻找。
那龟厌道也不认生,也不躲他,仿佛是见了故旧一般,一把抓了那鹤的长颈,口中欣喜了念叨:
“饶是嘴馋,倒是无有也。”
那怡和道长见这鹤如此的亲人,也是心下一个惊奇。
亦是一把抓了那鹤的长颈看了一眼鹤嘴,确定了道:
“嗯!是咱家养的。”
咦?这怡和道长怎识得?
倒是这茅山养这鹿鹤亦是个积年。
而这鹤亦是领地意识极强之物,几十只养在一起倒是一个不好共处,那叫一个经常的啄来爪去,饶是一番的热闹。
为了不让这帮家伙做出自家相残之事,从小便将那鹤嘴剪去一节。
那些个幼鹤吃疼便不再相互啄来。长大之后便是缘于那幼时记忆,再不敢乱啄,也能的一个各自相安的无事。
怡和道长亦是捏了鹤嘴又确认了,那龟厌见他如此,道:
“用你说嘴?若不是咱家养的,又如何缠了我要吃食?”
两人且在说话,却见那鹤挣脱了那怡和道长,又一头扎进那龟厌怀里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