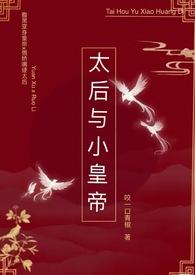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历史的回响:那些震撼人心的话语 > 第132章 汶上之风 闵子骞的拒仕操守(第3页)
第132章 汶上之风 闵子骞的拒仕操守(第3页)
战国时期,费邑成为齐国的领土(《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费宰不再是季氏的私臣,而是齐国的地方官员,职责转向“治民、征赋、守土”。考古现的战国“费丞之印”,说明此时费邑已设立辅佐费宰的官员,行政体系更加完善。
秦汉实行郡县制,费邑改为费县,费宰改称“费令”或“费长”,成为朝廷任命的正式官员。《汉书?地理志》记载东海郡有费县,其行政长官的职责是“劝农桑,平狱讼,恤鳏寡”,与春秋时期的费宰相比,权力受到中央政府的严格制约,不再有割据一方的可能。
唐代费县属沂州,县令的品级为“从七品下”(《唐六典》),其考核标准包括“户口增减、垦田多少、赋役完纳、盗贼多少”等,完全纳入中央集权的管理体系。此时的费县县令,与闵子骞拒绝的费宰已不可同日而语,成为普通士人施展治政才能的平台。
明清时期,费县县令的职责更加细化,除行政事务外,还需主持科举考试、兴修水利、兴办学校等。清代《费县志》记载,康熙年间费县县令朱约“修学宫,建书院,劝民垦荒,费民赖之”,其政绩与季氏时期的费宰形成鲜明对比——权力的性质已从私人工具转变为公共服务。
费宰职位的变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政治制度从“分封制”到“郡县制”的演进,也说明:同样的职位,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中,会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闵子骞拒绝的不是“费宰”这一职位本身,而是它在季氏专权体制下的不义属性。
十四、现代社会中的“汶上之风”:拒绝的当代意义
在现代社会,虽然没有“费宰”这样的职位,但闵子骞的“汶上之风”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拒绝不义”的精神,在各行各业都有生动体现。
职场中的拒绝:面对公司要求的“数据造假”“虚假宣传”,有人选择辞职,如某知名企业的财务总监因拒绝做假账而离职,虽失去高薪工作,却保住了职业操守;面对“996”的不合理加班制度,有人通过法律途径维权,用行动扞卫劳动者的权益。这些选择,与闵子骞拒绝季氏如出一辙——不被利益绑架,坚守职业底线。
商业中的拒绝:有些企业拒绝生产假冒伪劣产品,即使成本更高、利润更低;有些企业家拒绝“污染环境换展”,主动投入环保设备。如某纺织企业宁愿承受损失,也不使用有毒染料,最终凭借优质产品赢得市场。这种“拒绝”,是商业伦理的体现。
学术中的拒绝:面对“学术不端”“数据造假”的诱惑,有些学者坚守学术诚信,如某教授主动撤回有瑕疵的论文,即使影响职称评定也在所不惜。这种对真理的坚守,与闵子骞对道义的坚守一脉相承。
公共事务中的拒绝:公务员拒绝“权力寻租”,记者拒绝“有偿新闻”,医生拒绝“红包回扣”……这些拒绝看似微小,却共同构筑了社会的道德防线。正如闵子骞的拒绝改变不了季氏专权的现实,却能守住自己的操守,现代社会的每一次“拒绝”,都是对不义的无声反抗。
十五、闵子骞祠的千年香火:操守的物质传承
闵子骞的操守不仅通过文字流传,更通过祭祀建筑得以物质化传承。分布在山东、河南、安徽等地的闵子骞祠,成为后人缅怀先贤、砥砺操守的场所,千年香火不断,见证了“汶上之风”的持久生命力。
济南的闵子骞祠始建于西汉,现存建筑为明清重修,坐北朝南,由大门、正殿、东西配殿组成。正殿内供奉闵子骞塑像,头戴礼帽,手持竹简,神情庄重。祠内有一株千年古柏,枝干挺拔,相传为闵子骞亲手所植,象征其坚贞不屈的品格。每年农历二月二十四日(闵子骞诞辰),当地百姓都会举行祭祀活动,诵读《论语》中关于闵子骞的记载,这种习俗延续至今。
费县的闵子祠位于费邑遗址附近,据《费县志》记载,始建于唐开元年间,现存“闵子故里”碑为清代所立。碑文中“其心三月不违仁,其行一世不忘孝”,高度概括了闵子骞的品德。祠内的“拒仕亭”,亭柱上刻有楹联:“拒仕守仁心,汶水千秋照;孝亲传道义,泰山万代仰。”
河南范县的闵子骞祠,相传是闵子骞曾任范县县令时的住所,现存“闵子骞政绩碑”,记载他“治范期间,轻徭薄赋,兴修水利,百姓安居乐业”。这里的祭祀活动融合了当地民俗,既有儒家的礼仪,也有民间的祈福,体现了闵子骞形象的多元传承。
这些祠堂不仅是文物古迹,更是精神地标。它们提醒着后人:操守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选择;不是历史的陈迹,而是现实的指引。当人们走进祠堂,面对闵子骞的塑像,仿佛能听到他那句“善为我辞焉”的坚定声音,在心中激起对操守的思考。
十六、“孝”与“义”的现代诠释:闵子骞精神的当代转化
闵子骞的“孝”与“义”并非封建糟粕,而是可以进行现代诠释的精神财富,在家庭伦理和社会道德建设中仍能挥积极作用。
现代孝道的新内涵:闵子骞的“芦衣顺母”不是愚孝,而是“体谅与包容”。在现代社会,孝道可以表现为对父母的精神陪伴,而非盲目顺从;可以是平等沟通,而非等级服从。如定期与父母视频通话,尊重父母的生活方式,支持他们的兴趣爱好,这些都是“孝”的现代体现,延续了闵子骞“以德报怨”的包容精神。
社会道义的新表现:闵子骞的“拒仕”所体现的“义”,在现代社会表现为“社会责任”“职业道德”“公共精神”。如企业家的“慈善捐赠”,是对“达则兼济天下”的践行;志愿者的“公益服务”,是对“泛爱众”的诠释;普通人的“见义勇为”,是对“义之所至,不敢辞”的呼应。
孝与义的结合:闵子骞的孝与义是统一的,现代社会也需要“家庭美德”与“社会公德”的结合。一个对父母冷漠的人,很难对社会有责任感;一个缺乏社会良知的人,其家庭伦理也难免虚伪。如“最美孝心少年”不仅照顾生病的家人,还积极参与社区服务,展现了孝与义的现代融合。
闵子骞精神的当代转化,不是复古怀旧,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让传统美德在现代社会焕新的活力。正如费县闵子骞祠的宣传语所说:“学习闵子骞,居家尽孝,处世守义。”
十七、从“拒仕”到“有所不为”:中国文化的底线思维
闵子骞的“拒仕”体现了中国文化中深刻的“底线思维”——“有所为,有所不为”。这种思维不是消极的保守,而是积极的坚守,为个体和社会划定了不可逾越的红线。
个体的底线:在个人生活中,底线是“不伤害他人”“不违背良知”。如孔子所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孟子强调“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都是对个体底线的界定。闵子骞的底线是“不为不义之仕”,现代个体的底线可能是“不做亏心事”“不赚黑心钱”。
社会的底线:在社会层面,底线是“法律”“道德”“公序良俗”。《礼记?礼运》描绘的“小康社会”,以“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夫妇,以和兄弟”为底线,一旦突破这些底线,社会就会陷入混乱。如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正是因为诸侯、大夫突破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底线,才导致天下大乱。
底线的守护:守护底线需要勇气和智慧。闵子骞以“退至汶上”守护底线,孔子以“着《春秋》”褒贬善恶守护底线,后世的包拯以“铁面无私”守护司法底线,海瑞以“抬棺死谏”守护政治底线。这些守护虽然方式不同,却都体现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
在现代社会,底线思维尤为重要。食品安全的底线是“不添加有害成分”,环境保护的底线是“不破坏生态平衡”,公共安全的底线是“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这些底线的守护,需要个体的坚守、制度的完善和社会的监督,正如闵子骞的拒仕离不开孔子的肯定和后世的传颂,底线的守护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十八、闵子骞故事的民间传播:从正史到戏文
闵子骞的故事不仅在正史中记载,更在民间广泛传播,通过戏曲、评书、年画等形式深入人心,成为普通百姓的道德教科书,这种民间传播让“汶上之风”突破士大夫阶层,融入民族文化的血脉。
戏曲中的闵子骞:元代以后,以闵子骞为题材的戏曲大量涌现,除关汉卿的《闵子骞单衣记》外,还有明代传奇《芦衣记》、清代秦腔《鞭打芦花》等。这些戏曲往往将“芦衣顺母”和“拒仕汶上”结合,突出其“孝”与“义”的双重品质。在《鞭打芦花》中,有一段唱词:“芦花本是无情物,却教孝子受凄凉。若非真心孝感天,怎得阖家复团圆。”通过戏剧冲突,让观众在情感共鸣中接受道德教育。
民间故事中的闵子骞:在山东、河南等地的民间故事中,闵子骞的形象更加丰满。有故事说他拒仕后,在汶水岸边教书育人,当地百姓为了感谢他,自修建学堂;还有故事说他曾用自己的俸禄帮助贫困村民,“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的俗语就源于他的教导。这些故事虽无史料依据,却反映了百姓对理想人格的向往。
年画与剪纸中的闵子骞:明清时期的年画中,“闵子骞芦衣顺母”是常见题材,画面多为闵子骞跪在地上,父亲手持鞭子,后母站在一旁,弟弟躲在母亲身后,通过人物表情的对比,展现闵子骞的宽容和后母的羞愧。剪纸作品则多表现他“拒仕汶上”的场景,汶水波涛象征他不可动摇的决心。这些视觉艺术让不识字的百姓也能理解闵子骞的故事。
民间传播的过程,也是闵子骞形象不断被理想化的过程。百姓忽略了历史的复杂性,将他塑造为“完美无缺”的道德偶像,这种理想化虽然偏离史实,却体现了民间社会对“孝”与“义”的朴素追求,让闵子骞的精神得以在更广泛的群体中传承。
十九、季氏专权的经济基础:从土地掠夺到商业垄断
季氏能够长期专权,离不开强大的经济基础。他们通过土地掠夺、商业垄断等手段积累财富,控制鲁国的经济命脉,这种经济霸权与政治强权相互支撑,形成了难以撼动的权力网络。
土地兼并的加剧:春秋时期,鲁国实行“井田制”,土地归周天子所有,诸侯、大夫只有使用权。但季氏通过各种手段兼并土地,据《左传?昭公三年》记载,季氏“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将鲁国的土地和人口分成四份,季氏独占两份,孟孙氏和叔孙氏各占一份。到季平子时,更是“取卞”(《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将鲁国的重要城邑卞邑据为己有,土地面积远公室。
赋税制度的操控:季氏通过操控赋税制度,加重对百姓的剥削。他们改变鲁国传统的“什一税”(征收十分之一的赋税),实行“田赋”(按土地面积征税)和“丘赋”(按村落征兵和征税),据《左传?哀公十一年》记载,季康子“欲以田赋”,孔子反对说“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但季氏仍强行推行,将更多财富纳入自己腰包。
商业垄断的形成:费邑地处交通要道,是鲁国与齐国、吴国贸易的枢纽。季氏控制费邑后,垄断了当地的盐业、铁器、丝绸等贸易,从中获取巨额利润。《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春秋时期“子贡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着鬻财于曹、鲁之间”,子贡能在曹、鲁之间经商致富,也从侧面反映出鲁国商业的繁荣,而这其中相当一部分利益被季氏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