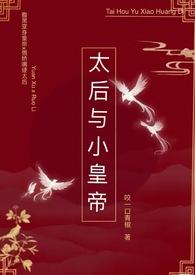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历史的回响:那些震撼人心的话语 > 第132章 汶上之风 闵子骞的拒仕操守(第2页)
第132章 汶上之风 闵子骞的拒仕操守(第2页)
闵子骞的拒仕,不是否定“仕”本身,而是否定“不义之仕”。儒家主张“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但前提是“邦有道”。孔子说“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论语?公冶长》),展现了士人“仕”与“不仕”的灵活选择。
有道则仕:当国家政治清明时,士人应积极出仕,施展抱负。《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在鲁国任大司寇时,“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将鲁国治理得井井有条。这种“仕”,是“达则兼济天下”的担当。
无道则隐:当政治黑暗时,士人应退隐自保,保持操守。孔子周游列国“干七十余君而无所遇”,晚年回到鲁国整理典籍,“笔则笔,削则削”,修《春秋》以明志。这种“隐”,不是消极逃避,而是“穷则独善其身”的智慧。
隐而不废:即使不仕,士人也可通过其他方式影响社会。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通过着书立说传播思想;东汉的郑玄,拒绝董卓、袁绍的征召,“括囊大典,网罗众家”,注疏群经,成为经学大师。这种“隐”,是另一种形式的“仕”。
闵子骞的拒仕,属于“无道则隐”,但他并未消极避世。《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记载,他“仕于鲁,为大夫”,只是拒绝为季氏服务。这种“选择性出仕”,展现了士人对“仕”的本质理解——仕是为了行道,而非谋禄;是为了利民,而非附势。
八、拒仕的代价与回报
拒绝一份高薪厚禄,需要付出实实在在的代价;但坚守操守,也会获得无形的回报。闵子骞的选择,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物质的清贫:《论语?雍也》记载,孔子称赞闵子骞“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但对他的生活状况却无记载,结合其拒仕的选择,可推测其生活清贫。陶渊明“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五柳先生传》),严光“披羊裘钓泽中”(《后汉书?严光传》),物质清贫是拒仕者的共同特征。
精神的丰盈:拒仕者虽然物质匮乏,精神却无比充实。闵子骞因拒仕赢得孔子的高度评价,成为“德行”科的代表人物;陶渊明在田园中找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真意;严光在富春江上获得“心与白云闲”的自由。这种精神丰盈,是对物质清贫的最好补偿。
历史的铭记:那些追名逐利的费宰早已被遗忘,而闵子骞的拒仕却被载入史册,代代传颂。费县的闵子祠,自汉代起香火不断;历代帝王对他屡有追封,唐开元二十七年追赠“费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琅琊公”。这种历史铭记,是对操守的最好回报。
社会的镜鉴:拒仕者的故事,成为社会的道德镜鉴。当官场腐败时,人们会想起闵子骞的坚守;当诱惑丛生时,人们会念叨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这种镜鉴作用,让拒仕的精神转化为社会的良知力量。
代价与回报的辩证法在此显现:失去的是暂时的利益,得到的是永恒的尊严;放弃的是眼前的官位,赢得的是历史的尊重。
九、季氏的权力与闵子骞的操守对抗
季氏在鲁国的专权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历经几代人的经营,形成了盘根错节的权力网络。闵子骞的拒仕,本质上是个体操守与强权政治的正面碰撞,这场碰撞揭示了权力与道德的永恒张力。
季氏的权力根基可追溯到季友。《左传?僖公十六年》记载,季友平定庆父之乱,辅佐鲁僖公,被赐汶阳之田及费邑,奠定了季氏的基业。到季文子执政时,“家无衣帛之妾,厩无食粟之马”(《国语?鲁语》),以节俭赢得民心;季武子则“作三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左传?襄公十一年》),将鲁国军队私有化,权力进一步扩张;至季平子,更是“与孟孙氏、叔孙氏共伐昭公”(《史记?鲁周公世家》),把鲁昭公赶出鲁国,开启了“陪臣执国命”的时代。
季氏专权的核心是“僭越”。他们不仅在军事、经济上掌控国家,更在礼仪上挑战周天子权威。《论语?八佾》详细记载:“季氏旅于泰山”,祭祀本应由天子主持的泰山之神;“季氏舞八佾”,使用六十四人的舞蹈队伍,远诸侯应有的三十六人规格。孔子对此痛心疾,认为这是“天下无道”的标志——“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论语?季氏》)
闵子骞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个“陪臣执国命”的季氏。费邑作为季氏的根据地,是其对抗公室、控制鲁国的重要筹码。任命闵子骞为费宰,既有拉拢人才的意图,也有将其纳入权力体系的考量——如果连以德行着称的闵子骞都接受任命,季氏的统治就更具“合法性”。
但闵子骞的操守像一把利剑,刺破了季氏的伪装。他的拒绝传递出明确信号:权力可以收买利益,却无法收买良知;可以控制疆域,却无法控制人心。这种对抗在当时产生了深远影响,《孔子家语?颜回》记载,孔子听闻闵子骞拒仕后,赞叹道:“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亦不间于其君大夫之言。”这里的“不间于其君大夫之言”,正是对他不屈服于强权的肯定。
季氏对闵子骞的拒绝并非无动于衷。据《礼记?檀弓》记载,后来季氏又想任命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固辞”,甚至“退而之汶上”,用实际行动表明立场。季氏最终未再强求,这既显示了闵子骞的坚定,也反映出强权对德行的某种忌惮——即使在黑暗的政治环境中,道德的光芒仍能让权力有所收敛。
十、闵子骞的教育实践:拒仕后的行道方式
闵子骞拒绝为季氏服务后,并未消极避世,而是选择以教育传播道义,这种“退而育人”的方式,成为他行道的另一种途径。
在曲阜孔庙的“圣迹殿”中,有一幅“闵子骞讲学”图:他坐在杏坛之上,弟子们环坐四周,手中捧着竹简,神情专注。图中背景是简陋的茅屋,与季氏的宫殿形成鲜明对比,却洋溢着浓郁的学术气息。这幅图虽为后世所作,却真实反映了闵子骞的教育实践。
闵子骞的教育内容以儒家伦理为核心,尤其注重“孝”与“义”的传授。《孔子家语?弟子行》记载,他教导弟子“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将家庭伦理扩展到社会伦理。他的教学方法灵活多样,常以自身经历为例,如讲述“芦衣顺母”的故事,让弟子理解“孝”不仅是顺从,更是包容与关爱。
他的弟子中不乏后来的贤达之士。《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索引记载,闵子骞的门人“有若、曾参之流”,虽未必直接受教,却深受其思想影响。有若提出“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与闵子骞的谦和品格一脉相承;曾参强调“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也体现了对道德操守的重视。
闵子骞的教育实践,展现了士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另一种可能——当仕途受阻时,教育成为传承道义的薪火。这种“退而不休”的精神,影响了后世无数教育家: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孟子?滕文公下》),周游讲学传播思想;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授徒,着书立说”,将理学扬光大。
十一、汶上意象的文学演绎:从《论语》到后世诗词
闵子骞“必在汶上”的宣言,让汶水成为文学作品中的重要意象,历代文人墨客以此为题,抒对操守的赞美与坚守。
汉代《古诗十九》中有“汶水汤汤,行人思乡”之句,虽以汶水写乡愁,却隐约可见闵子骞故事的影子——汶水不仅是地理界限,也是情感与精神的寄托。
唐代李白在《古风?其五十一》中写道:“殷后乱天纪,楚怀亦已昏。夷齐是何人,独守西山饿。”虽未直接提及闵子骞,却与“汶上之风”精神相通,借伯夷、叔齐赞美坚守气节之人。杜甫则在《壮游》中感叹:“朱门任倾夺,赤族迭罹殃。国马竭粟豆,官鸡输稻粱。”通过批判权贵的奢侈,反衬拒仕者的高洁。
宋代苏轼对闵子骞尤为推崇,在《送颜复兼寄王巩》中写道:“颜回屡空安乐在,闵子单衣顺良存。”将闵子骞与颜回并列,肯定其在贫困中坚守操守的品质。他在《和子由蚕市》中“蜀人衣食常苦艰,蜀人游乐不知还”的对比,暗含对“不义之乐”的批判,呼应了闵子骞对季氏富庶的拒绝。
元代关汉卿在杂剧《闵子骞单衣记》中,详细演绎了“芦衣顺母”和“拒仕汶上”的故事,将闵子骞塑造为“孝”与“义”的完美化身。剧中闵子骞拒绝季氏时唱道:“俺只守着孔圣人的道理,不当那权臣的鹰犬。”直白表达了对操守的坚守。
这些文学作品中的汶上意象,已越地理范畴,成为操守、气节、道义的象征。文人墨客通过吟咏闵子骞的故事,既表达对现实中趋炎附势者的不满,也寄托了自己对理想人格的追求。
十二、闵子骞与同时代士人的操守比较
春秋末期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士人群体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选择,闵子骞与同时代士人的不同选择,构成了一幅幅生动的操守画卷。
与孔子的比较:孔子周游列国,“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试图在乱世中寻找行道的可能;闵子骞则选择“不义则不仕”,划清界限。两人方式不同,目标一致——孔子是“积极入世的坚守”,闵子骞是“消极避世的抗争”。孔子对闵子骞的欣赏,正是对这种不同方式的认可。
与子贡的比较:子贡善于外交与经商,“存鲁、乱齐、破吴、强晋”(《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在复杂的利益格局中周旋;闵子骞则坚守原则,拒绝任何妥协。子贡是“在游戏中改变规则”,闵子骞是“不进入不义的游戏”,代表了士人应对乱世的两种策略。
与子夏的比较:子夏“仕于魏文侯”(《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为魏国的强盛制定礼仪制度,是“以道事君”的代表;闵子骞拒绝为季氏服务,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体现。子夏的选择需要智慧,闵子骞的选择需要勇气,两者都是对“道”的坚守。
这些比较揭示:操守并非只有一种表现形式,重要的是在任何选择中都不放弃原则。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子贡的“权变”,子夏的“服务”,闵子骞的“拒绝”,共同构成了儒家士人的操守光谱。
十三、“费宰”职位的历史变迁:从权力象征到职能转变
费宰这一职位随着历史变迁,其性质和意义也生了变化,从季氏专权的工具,逐渐演变为普通的地方行政官职,这种变迁反映了政治制度的演进和社会观念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