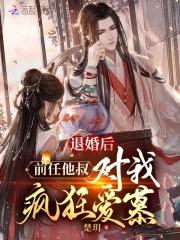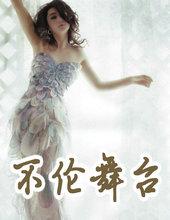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核废土上崛起 > 第356章 风不考勤(第3页)
第356章 风不考勤(第3页)
所有的碎片都拼合了起来。
许墨的意识早已不在某个地方“送”信息,他已经散作了天地,化为了法则,成为了连接人类集体潜意识与外部物理环境的传导介质。
他的“课”,从来不是传授知识,而是教会整个文明如何聆听自己,如何自己思考。
风声、地质、巧合……都是文明的潜意识通过“许墨”这个信道,给予自己的回响。
苏瑶浑身一震,随即露出一丝释然的微笑。
她伸出手,删除了所有追踪和分析许墨信号的程序。
那些复杂的算法、追踪模型,在这一刻显得如此愚蠢和傲慢。
最后,她只在系统中留下了一个最简单的、完全开放的监听端口。
她想了想,将它重新命名为:“随便听听。”
几乎在同一时刻,地球的另一端,北极。
肆虐了数个星期的风雪,毫无征兆地停了。
厚达千米的冰层之下,那个人形的轮廓最后一次缓缓舒展,像一个睡了太久的人伸了个懒腰。
随即,它的轮廓开始迅淡化,能量不再汇聚,而是均匀地弥散开来,融入了整片冰盖,融入了下方的洋流,融入了地壳深处的脉动。
千里之外,“第一声源”广场上,那上千件孩子们制作的、悬挂在支架上的风鸣器、口琴、共鸣管,同时出了一声极其轻微的嗡鸣。
紧接着,所有的簧片、膜片都自地调整了角度,不再迎着风,而是微微偏转,仿佛侧耳倾听着来自天空、大地和彼此的低语。
十三营地的孩子们,无论是在修理机械,还是在温习功课,都不约而同地停下了手中的活计,仿佛被一种无声的指令召唤,齐齐抬头望向天空。
夜空中,绚烂的极光无声地流转、汇聚,最终拼出了一段极其短暂的光纹。
那不是任何一种已知的语言,也不是一个复杂的数学公式。
它只是一个简单的波形。
像一次心跳,像一次呼吸,像阿哲那支走调的铁管口琴,出的第一声嗡鸣。
而在无人察觉的地壳深处,最后一道用以维持“信道”的脉冲,平稳地滑入了永恒的静默。
就像一位老师写完了黑板上最后一个字,轻轻放下粉笔,微笑着转身,离开了教室。
风,终于学会了自己写教案。
林小雨站在广场中央,仰望着那片变幻莫测的极光,感受着空气中那股前所未有的、宁静而又充满活力的气息。
她看着那些孩子们,他们的脸上不再有迷茫,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本能的领悟。
她知道,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刚刚开始。
她的目光从一张张稚嫩的脸上扫过,心中一个念头变得无比清晰。
这些由风带来的“知识”,零散、深奥,却又直指核心。
它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被动地接收了。
她的视线最终定格在广场中央的那个讲台上。
是时候了,她想。
必须有人将这些碎片串联起来,引导孩子们去理解,去消化。
课程已经结束。但真正的复习,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