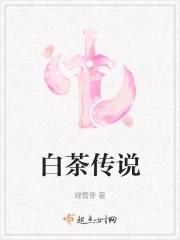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了解历史之大汉王朝 > 第11章 柴荣三征南唐与李煜的困兽之斗(第1页)
第11章 柴荣三征南唐与李煜的困兽之斗(第1页)
上回书咱们说到,柴荣二征南唐,一手靠工程师的“水轮炮”“浮桥”破了寿州城的天险,一手靠赵匡胤夜袭紫金山,把李景达的五万援军打得溃不成军。这座啃了近一年的“硬骨头”终被拿下,淮南半壁江山彻底落入后周手中。而李煜在金陵城里,装病躲不过、拜佛求不来、写骈文被柴荣当成笑料,除了对着战报唉声叹气,竟拿不出半点像样的对策。可这五代乱世从不等沉溺的君主,柴荣刚在寿州城安抚完百姓,就已开始打磨三征的刀枪;李煜则被逼到了墙角,不得不硬着头皮开启“困兽之斗”,南北双方的终极较量,眼看就要在长江两岸拉开帷幕。
先说柴荣这边,拿下寿州后,他没急着班师回朝,反而把中军大营设在了寿州,天天召来赵匡胤、李重进等将领推演战局。御案上摊着新绘制的长江流域地图,柴荣的手指沿着长江北岸一路滑动,最终停在濠州与泗州之间:“前两次南征,咱们拿下了淮南十四州,如今南唐的防线只剩长江天险。第三次南征,朕要让大军从这里渡江,直扑金陵!”
为了突破长江,柴荣又祭出了“技术流”——他让随军的工程师们沿着淮河打造大型战船,还特意从吴越国招募了一批熟悉水战的水手,编入后周水军。工程师们日夜赶工,造出的战船不仅体型庞大,还在船舷两侧加装了铁板,既能抵御弓箭,又能撞沉南唐的小船。赵匡胤则带着士兵在淮河上演练水战,从登船、划桨到水上列阵,一遍遍反复操练,原本只擅长陆战的后周军,渐渐有了水军的模样。
有大臣劝柴荣“休养生息,再图南征”,柴荣却摇了摇头,指着地图上的金陵:“李煜现在就像惊弓之鸟,咱们一停,他就会缓过气来。趁他病要他命,这才是灭唐的最好时机!”说罢,他下旨从汴梁调运粮草、兵器,源源不断送往淮南,整个后周就像一台高运转的机器,全力为三征南唐做准备。
再看金陵城里的李煜,寿州失守、援军溃败的消息像两座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徐铉等大臣天天在殿上劝谏,让他“整顿长江防线、招募士兵”,连一直不问政事的小周后都忍不住劝他:“陛下,就算不求胜,也得守住长江,不然金陵就成了空城!”
李煜这才终于从诗词里抬起头,被逼着开启了“困兽之斗”。可他的“备战”,依旧透着文人的慌乱与外行——他先是下旨“招募勇士守长江”,却没规定粮饷、军饷,百姓们怕白白送死,没几个人愿意参军;后来又听信宦官的建议,把金陵城里的百姓强征来加固城墙,连老人、孩子都被拉来搬砖石,弄得民怨沸腾。
最荒唐的是,他竟让宫廷乐师谱写“战歌”,让士兵们在守城时传唱,说“歌声能壮士气”。乐师们硬着头皮写了《保江南》,歌词满是“长江天险不可破,南唐江山万年固”的空话,士兵们唱着别扭,听着更没底气。徐铉见了,急得直跺脚:“陛下!士兵要的是粮食、兵器,不是空泛的歌声啊!”可李煜却固执地说:“士气振了,才能守住城,你不懂!”
即便如此,南唐也并非全无抵抗之力。老将林仁肇在紫金山兵败后,收拢了残兵,驻守在长江南岸的采石矶——这里是长江最窄的地方,也是后周最可能渡江的地点。林仁肇亲自带着士兵在江边搭建防御工事,在水里插满尖木,还把战船排成“一字阵”,日夜巡逻,誓要“与采石矶共存亡”。他还上书李煜,请求“主动出击,烧掉后周的战船”,可李煜怕激怒柴荣,硬是压下了奏疏:“林将军,咱们只要守住就行,别主动惹事。”
林仁肇看着驳回的奏疏,气得拍了桌子:“陛下这是把南唐的江山,当成了能靠忍让保住的玩物!”可他终究是臣子,只能咬着牙加固防线,眼睁睁看着后周的战船在淮河上越来越多。
此时的长江两岸,一边是柴荣摩拳擦掌,战船列阵待,士兵们士气如虹;一边是李煜慌慌张张,备战乱象丛生,只有少数将领还在苦苦支撑。这场三征南唐的大战,究竟是柴荣一举渡江灭唐,还是李煜能靠长江天险再撑一阵?林仁肇的防线能否挡住后周的铁蹄?赵匡胤在这场大战中,又会立下怎样的功劳,为自己的未来再添筹码?这五代乱世的终局之战,已悄然拉开了序幕。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
一、周军砺海:柴荣打造两栖劲旅,李煜惊闻周师渡淮
显德五年(公元957年)的春天,阳光明媚,微风拂面。汴梁城外的汴河两岸,一片繁忙景象。叮叮当当的打铁声和工匠们嘹亮的号子声交织在一起,仿佛是一曲激昂的交响乐,在空气中回荡。
这里正是柴荣大张旗鼓打造战船的地方。他决心为即将到来的三征南唐之战亮出“终极必杀技”,一举攻克南唐。河岸上,数十艘战船的龙骨已经初具雏形,它们犹如沉睡的巨兽,静静地横卧在河边。工匠们忙碌地穿梭其中,有的在铺设船板,有的在安装桅杆,每个人都全神贯注,不敢有丝毫懈怠。
不远处的空地上,数百名北方士兵身着湿漉漉的铠甲,正紧张地进行着训练。他们在吴越籍水军将领的指导下,练习着游泳和划船技巧。水花四溅,溅湿了士兵们的衣襟,但他们毫无怨言,因为他们知道,只有通过艰苦的训练,才能在战场上取得胜利。
柴荣站在岸边,凝视着这一切,心中充满了期待。他相信,这些精心打造的战船和训练有素的士兵,必将成为他征服南唐的利器。
在此之前,后周已经进行了两次南征,但尽管在陆地上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却始终无法突破南唐的长江天险。这主要是因为后周军队不擅长水战,面对汹涌的江水和南唐强大的水军,他们显得束手无策。
柴荣作为后周的皇帝,对这种局面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明白,如果想要彻底消灭南唐,就必须克服“北方人不善水战”的固有观念,打造一支强大的水军。于是,他下定决心,从国库中拨出大量的资金,用于建造战船和训练水军。
为了能够迅提升水军的实力,柴荣还采取了一项重要的举措——派遣使者前往吴越国。他以“共分南唐疆土”为诱饵,成功借调了二十名精通水战的将领。这些将领都是吴越国的精英,他们常年在钱塘江和长江流域作战,对当地的水流、风向等自然条件了如指掌,拥有丰富的水战经验。
对于后周来说,这些将领无疑是急需的“活水”。他们的到来,不仅带来了先进的水战技术和战术,还为后周的水军注入了新的活力和信心。在这些将领的指导下,后周的水军开始迅崛起,逐渐掌握了水战的技巧和要领。
这一天,阳光明媚,柴荣身着龙袍,意气风地亲自来到了造船工地。他的步伐稳健有力,每一步都似乎带着一种威严和决心。
工地上,工人们正忙碌地建造着一艘艘巨大的战船,他们的汗水在阳光下闪耀着光芒。柴荣饶有兴致地观察着这些战船,不时询问工人们一些技术问题,对他们的工作表示赞赏。
突然,一阵激昂的号角声响起,吸引了柴荣的注意。他转头望去,只见一队士兵正在操练,他们的动作整齐划一,气势磅礴。柴荣满意地点点头,然后对手下的将领们笑道:“前两次咱们在陆地上杀得南唐丢盔弃甲,让他们以为咱们只会骑马射箭。这次,朕要让李煜知道,水里也不是他们的地盘!”
他的声音中透露出一种自信和霸气,将领们纷纷附和,表示一定不辜负皇帝的期望。柴荣看着这些训练有素的士兵,心中充满了信心,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一定能够在水战中取得辉煌的胜利。
有个出身骑兵的将领没底,小心翼翼地凑上前:“陛下,咱们北方将士从小骑马,连大河都少见过,这战船、水战的门道太复杂,真能玩转水军?”
柴荣闻言,猛地一拍身边的船板,震得木屑簌簌掉落,语气里满是不服输的劲:“不会就学!朕当年刚继位时,也没人信朕能打赢北汉、契丹!兵法说‘兵无常势’,只要肯下苦功,北方人照样能在水里打胜仗!朕就不信这个邪!”
为了让水军快成型,柴荣下了死命令:士兵每日必须在水里操练四个时辰,学不会游泳者,罚俸禄;水军将领需每日提交训练报告,完不成进度者,降职使用。他还常亲自来到河边,看着士兵们练习登船、列阵,甚至会坐上小船,跟着吴越将领学习辨认水流——原本对水战一窍不通的后周军,经过数月苦练,竟真练出了模样:战船能在淮河上整齐列阵,士兵能熟练操控船桨、射弩箭,连最棘手的“水陆协同”战术,都能顺畅演练。
同年十月,后周水陆大军集结完毕。柴荣在汴梁城外举行誓师大会,十万大军列阵如黑云压城,战船沿着汴河排开,帆影连天,军旗上的“周”字在风中猎猎作响。柴荣身披亮银铠甲,手持佩剑,站在高台上对着将士们高声喊话:“南唐占江淮百年,割据一方,百姓苦之久矣!这次咱们水陆并进,直捣金陵!谁能第一个拿下李煜的皇宫,朕就封他当节度使,赏钱万贯!”
士兵们听得热血沸腾,纷纷举起兵器高喊:“拿下金陵!活捉李煜!”喊声震得汴河水面泛起涟漪,连远处的树木都微微晃动。当天,柴荣亲自率领水陆大军,沿着汴河南下,目标直指长江北岸的南唐重镇——濠州。
消息传到金陵,南唐朝堂瞬间乱成一团。大臣们围着李煜,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宰相冯延巳颤巍巍地说:“陛下,后周打造了大批战船,还借了吴越的水军将领,显然是要渡江南下!咱们得赶紧加固长江防线,在采石矶、瓜洲渡多派士兵,再把战船集中起来,绝不能让周军过江啊!”
可李煜却坐在龙椅上,目光落在案头未完成的词稿上,那是他昨夜刚写的《浪淘沙令》,还没斟酌好最后两句。他抬起头,幽幽地叹了口气,语气里满是侥幸:“冯相不必惊慌。长江宽达数十里,风大浪急,后周的北方人就算练了几天水战,也未必能驾驭得了。长江天险,岂是那么容易突破的?”
话音刚落,殿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内侍总管跌跌撞撞地跑进来,脸色惨白:“陛下!不好了!探子来报,后周水军已经渡过淮河,拿下了濠州城外的渡口,现在正朝着泗州方向进军!”
“什么?”李煜猛地从龙椅上站起来,手里的毛笔“啪嗒”一声掉在词稿上,墨汁瞬间晕染开来,把“帘外雨潺潺”的词句涂成了一团黑。他瞪大了眼睛,声音带着难以置信的颤抖:“他们怎么做到的?北方人……怎么可能这么快渡过淮河?”
他始终以为,长江天险能护南唐周全,却忘了淮河是长江的支流,后周一旦掌控淮河,就能顺着河道直抵长江。此刻的李煜,看着案上被墨汁弄脏的词稿,又想起内侍口中“渡过淮河的后周水军”,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所谓的天险,在柴荣的决心与后周的实力面前,竟如此不堪一击。而南唐的命运,也随着这支“水陆两栖战队”的南下,彻底走到了悬崖边缘。
二、金陵困守:李煜全民皆兵挽危局,外交忽悠遇冷遇
后周水军渡过淮河、直逼长江的消息,如同一道晴天霹雳,狠狠地劈在了沉溺在诗词世界中的李煜身上。这突如其来的消息,犹如一把锋利的尖刀,无情地刺破了他那虚幻的文学梦境,将他从沉醉中猛然惊醒。
李煜瞪大了双眼,满脸惊愕地望着眼前的奏报,心中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慌。他意识到,自己不能再继续沉迷于诗词之中,而对国家的安危视若无睹了。
于是,他迅收起了平日里的懒散与懈怠,一改往日的颓废模样,在金陵皇宫里紧急召集大臣们召开朝会。
朝堂之上,气氛凝重而肃穆。李煜面色凝重地坐在龙椅上,他的声音虽然有些低沉,但却透露出一种决然与果断:“诸位爱卿,如今后周水军来势汹汹,已渡过淮河,直逼长江。我大江南岸危在旦夕!”
说罢,他猛地一拍御案,站起身来,厉声道:“即日起,金陵及周边州县全民皆兵!凡十五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男子,皆需参军守城!不得有丝毫延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