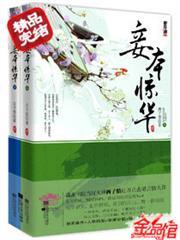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重生觅良婿,偏执权臣他总想抢亲 > 第108章 一片心意(第2页)
第108章 一片心意(第2页)
白怀瑾那压抑到极致的静默,那不是痊愈的征兆,而是火山喷前的死寂。
此刻,听着父亲竟然提议将这位“闷葫芦”请入家中宴饮,联想到这看似寻常家宴下母亲为妹妹牵线的深层意思。
桑知胤的目光在依旧平静的桑知漪脸上停驻了一瞬,又迅转向父亲桑凌珣,心念电转间已有了计较。
“父亲说得是!既如此,请客自然贵在热闹尽兴!多请几位朋友才更好!”他脸上露出爽朗的笑容,看向桑凌珣和柳氏,“正好,我同窗好友戚隆,前日还在念叨许久未见我了,不如一并请了他来?他是个爽利豪侠性子,最会暖场子!”
桑知胤语略快,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希冀,仿佛真的只是为了增添席间热闹气氛,顺带完成对好友的邀约。
唯有搭在座椅扶手上的左手拇指和食指,无意识地轻轻捻动着一枚冰凉的玉扳指。
窗外,冬日的阳光虽亮,却没什么温度。
暖炉里的香灰轻轻爆裂了一声,更衬得厅堂里短暂的寂静。
柳氏闻言,脸上浮现出宽和的笑容,自然地点点头:“胤儿想得周到。戚家那孩子爽利,是能活跃气氛。老爷?”她征询地看向丈夫。
桑凌珣深邃的目光在儿子那张带着明朗笑容的脸上停驻片刻,又掠过他捻动扳指的微末动作。
心中了然,面上却不露分毫,只沉吟着颔:
“可。”
……
隆冬岁末的京都,屋檐垂挂着晶莹的冰凌,映着稀薄的日光。
平日里总是矜持而规律的日子,到了年关反倒显出几分寂寥。
桑知漪如常地处理着自家一应简单事务,闲暇时或看书习字,或摆弄园中花木,日子过得闲适却也疏离。
除却娘家父母兄姐,她甚少主动在京中亲友间走动。那些迎来送往、曲意逢迎的应酬,于她而言,远不及一方小院来得清净自在。
只是偶尔回府小坐,看到兄长桑知胤被迫陷入永无止境的相亲局,被母亲柳氏用各种名目按在席间应对那些或端庄或活泼的闺秀时,他眉宇间那抹竭力掩饰的烦躁与无奈,总让她心头泛起一丝酸涩。
她心知兄长真正的姻缘尚未至,那位能与兄长琴瑟和鸣的女子,还要迟些时候才会出现。
这念头在她舌尖转了又转,最终也只能化作心底一声无声的叹息。
未来之事不可言,纵有先知也无凭,唯有余生默默祈盼。
这日,桑知漪早早起身。
深冬寒气侵骨,她却未乘那架铺着暖裘的华丽马车上街,只吩咐了车夫套上普通青帷小车。车轮碾过铺着薄雪的青石街道,出有节奏的吱呀声。
车子最终停在城南一条相对僻静却不失整洁的巷口。
门楣上悬挂的木匾刻着三个古拙的大字——“玄月堂”。
推开略显厚重的木板门,里面的暖意混着一种无法彻底驱散的尘嚣味扑面而来。
深冬时节,京中真正的贫苦人家也需阖家守岁,来此求助或帮手的显贵人等更是稀少了许多。大堂里略显空荡,唯有角落里几个衣衫虽旧却还干净的妇人在帮着整理分类一些琐碎物品。
“桑小姐来了。”管事章伯是个上了年纪的干瘦老头,此刻正蹲在地上,就着天窗漏下的光线仔细核对一本厚厚的账簿。
他抬起头,脸上的皱纹在昏暗中堆成更深的沟壑,招呼声里带着熟稔的亲近,只扬了扬下巴示意:“里面东三库房里,这两日新到的一批东西刚清点完,只粗粗堆着,还得劳烦您帮着理出个头绪来。”
桑知漪点点头,褪下厚厚的鹤氅交给旁边一个手脚麻利的小丫头,露出里面那身便于活动的藕荷色交领窄袖棉袍。
她挽起袖子,径直朝章伯所指的库房走去。
沉重的仓库门推开,寒意和积尘的气味扑面而来。
堆叠的麻袋占据了小半个空间,角落里还杂陈着各式匣子、包袱、成匹的布帛,甚至几篓干硬的馒头,显是各处府邸捐赠过冬的米粮衣物,因年关人手短缺,一时尚未及细查整理。
桑知漪敛了神色,并无半分嫌恶。
她上前,熟练地打开一只蒙着灰的楠木箱,里面是十几件半新不旧的裘袄皮料,毛色杂乱,显然来自各处。
她一件件取出,摩挲查看,按成色、质地、大小分门别类叠好。又掀开一个篓子,里面是硬邦邦看不出形状的馒头饼糕,已有些干裂,她小心捡出勉强还能食用的部分,放入旁边干净的布袋。
接着是布匹,成堆的素绢葛布凌乱地码放着,桑知漪一匹匹展开,丈量尺寸,归拢放置……她不急不躁,动作麻利却极有条理。
偌大的仓库,只闻她轻微的窸窣翻捡声,落下的尘土在微弱的光线中无声翻腾。
日影在紧闭的窗纸外一点点西斜,库房内的光线愈暗淡。直到腿脚都有些酸麻,堆满屋角的杂乱才终于有了整齐的轮廓,按用途成色堆列着,等着年后再分各处。
“辛苦二小姐了!”章伯不知何时走了进来,看着被打理得井井有条的库房,脸上露出真心的笑。他搓了搓被寒气冻得有些僵硬的手,没等桑知漪去净手,便从自己随身的旧布褡裢里掏出一个小小软软的包袱,递了过去。
那包裹用的蓝布洗得白,边角有些磨损,却干干净净。
“这是?”桑知漪微微讶异。
章伯笑得慈祥,压低了点声音:“早前那位腿脚不方便的张婶子、还有西城根下带着三个娃熬日子的春娘……您记得不?年前您来帮过她们好几回。前日她们得点空凑了点东西托我带给您,不值钱,连针线都是粗的,可都是她们的一份心。没等到您,这不,就求我务必转交到您手上。”
桑知漪小心翼翼地接过那小小的包袱,指腹能感受到包裹布料的粗粝。
她并未立即打开,只望向章伯。老人那双在暗淡光线下显得有些浑浊的眼睛里,充满了理解与欣慰。
她心中了然。
这些妇人,寒冬腊月里,每一粒米都要算计着下锅。这点心意,许是她们从牙缝里省下几口吃食换了尺粗布,又或是在油灯下熬红眼,一针一线费力缝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