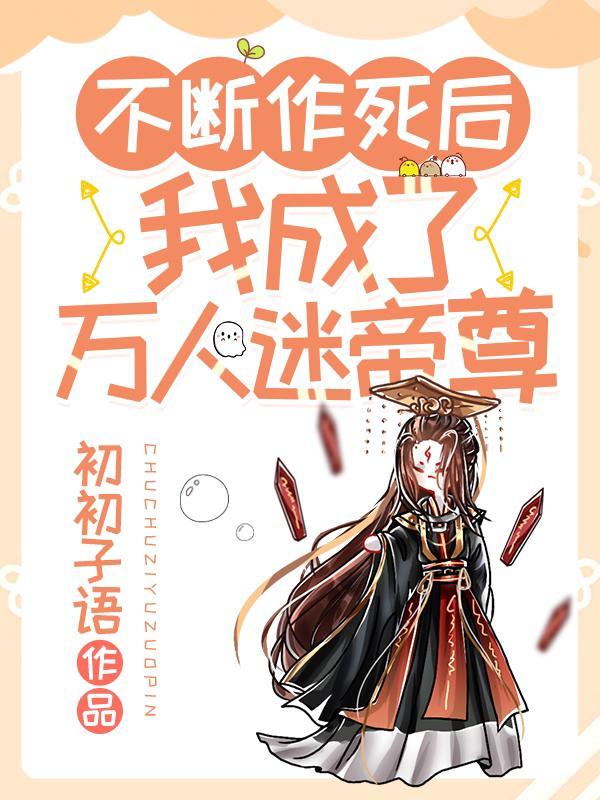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蜀汉之庄稼汉 > 第1478章 朕实不知(第2页)
第1478章 朕实不知(第2页)
以张苞领征东将军,督王含、刘浑、秃阗立、夏侯霸等部五万,进驻谯县,临淮水而立寨;
以姜维领镇南将军,督柳隐、石苞、毋丘俭等部五万,移屯南阳,扼襄樊之咽喉;
以傅佥领翊军将军,与杜预、马谡等将三万,聚于汉中东三郡,舟师具舳舻以待;
以张嶷领安南将军,督罗宪、王濬等部三万,整顿永安水寨,修艨艟战船。
关中八军余者皆秣马厉兵,旦夕可出武关。
诏书既下,长安武库昼夜锤击之声不绝,如巨兽磨牙。
有江东细作窃观长安官道粮车络绎不绝,尘土蔽日如黄龙腾空,连夜遁走报于建业。
延熙十四年,即吴建兴元年。
暮色如一方沉甸甸的玄色锦缎,将秦淮河水与石头城垣缓缓裹紧。
一辆沾满尘泥的安车,自西面覆舟山方向辘辘驶来,悄无声息地滑入宫城侧门。
宫门前,御者高擎使节旌旗——赤帛为底,墨绣“吴”字,边缀九旒牛尾。
守门都尉见之,不敢怠慢,验过铜符鱼契,亲自引车入内。
车帘掀开,一人几乎是滚落般跌出,官袍皱如咸菜,冠缨歪斜,面色在宫灯映照下惨白如丧,正是秦博。
他怀中紧抱一具紫檀木函,一见禁卫,嗓音嘶哑:
“陛下……、带我去见陛下!汉主有亲笔国书,嘱咐我要亲呈御前。”
不过半柱香功夫,秦博已跪在了一处偏殿的冰纹砖地上。
面前之人,面白无须,眼细如缝,正是中常侍岑昏。
他并未急着去接那木函,只慢条斯理地用银签拨亮了一盏雁足灯。
灯火跳跃,将他身影拉长,投在绘有云气仙鹤的殿壁上。
“秦君,辛苦。”岑昏声音尖细平稳,“汉主……如何说?”
秦博浑身一颤,似想起大司马府上那冰锥般的目光与诛心之言,竟伏地哽咽起来,语无伦次:
“汉主……大司马怒极……言丞相,背盟联魏,若陛下不剖白此事,就要兵南下攻我大吴,我归来时,听说商路也断了……”
听到秦博这个话,岑昏不禁眉头一皱,究竟是汉主还是大司马?
然见秦博冠堕散,涕泗横流的模样,知他已近崩溃,神智混乱。
他的细眼眯得更紧,俯身取过木函。
开启,取出绢书,就着灯火细看。
他读得很慢,每一个字都像在舌尖咀嚼。
殿内只闻秦博压抑的抽泣与灯芯偶尔的噼啪声。
良久,岑昏指尖在“诸葛恪私联篡逆”几字上轻轻摩挲,这才缓缓卷起绢书,细眼微眯。
接着,眼中闪过一抹冷意。
“秦君劳苦,且在此安心歇息。陛下处,老奴自有分说。”
他转身,对侍立的小黄门低声吩咐,声音却足以让秦博听清:
“去丞相府,告知当值郎官:秦君已归,然旅途劳顿,邪风入体,病势沉重,已由太医令遣医工诊治。”
“汉主国书,秦君既负亲呈之命,某不敢僭越,已暂存禁中。夜漏已深,宫门落钥,请丞相勿忧,待明日朝会,陛下当躬亲示之。”
小黄门领命而去。
岑昏看着秦博被扶往后殿“休养”,这才又招手唤来另一名绝对心腹的小宦,声音压得极低,几不可闻:
“往吕中书府邸,走夹道旧门。就说……‘长安帛书至,时机至矣!’”
不过一刻,吕壹府邸的书房里,吕壹刚听完岑昏心腹的耳语,手中把玩的一枚“平准”铜印“当啷”一声落在紫檀案几上。
铜雀灯基上的烛光,映着吕壹阴晴不定的脸。
良久,他这才从喉间挤出一声似哭似笑的低喃:
“果然……果然来了!”
自诸葛恪掌权以来,校事府权柄尽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