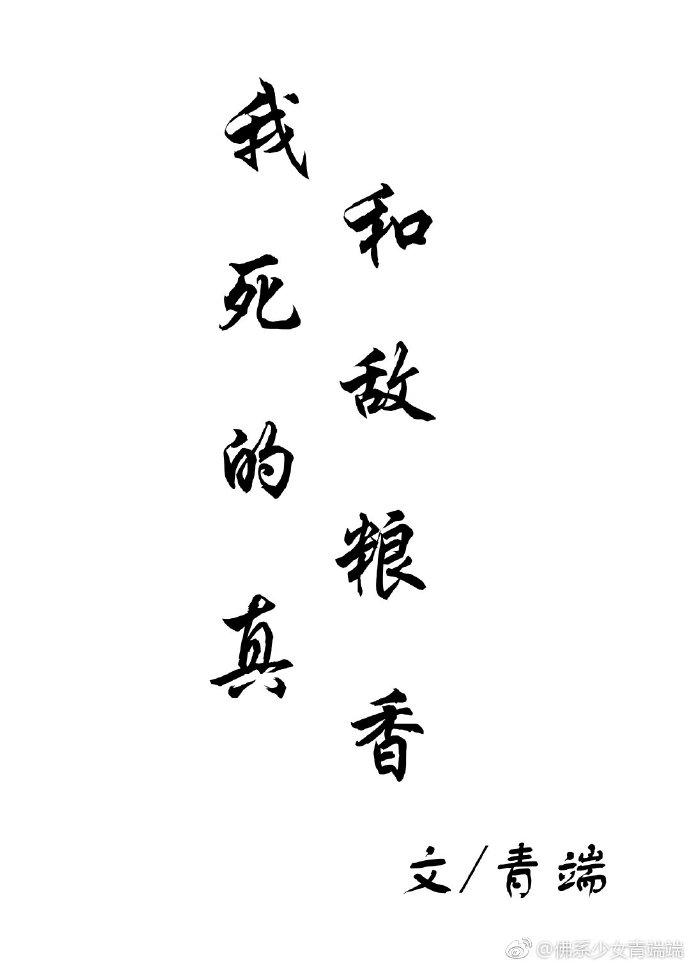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恢复视力后,发现夫君换人了 > 第六十四章 谢充有阿娘她也有(第2页)
第六十四章 谢充有阿娘她也有(第2页)
疲惫、伤痛、后怕,以及山洞内令人窒息的寒意,瞬间将她淹没。
眼皮重若千斤,她用力眨了眨眼,想保持清醒,至少等到玄十二、十三找来,或者……天光再亮些。
可视线却越来越模糊,跳跃的火光,江敛苍白的侧脸,都开始旋转扭曲。
耳畔呼啸的风声也渐渐远去,终于,支撑到了极限。
她头一歪,彻底失去了意识。
黑暗,温暖。
然后是刺骨的寒风夹杂着雪沫,拍打在她脸上。
她好像……变矮了,视野也变得低了许多。
四周是白茫茫的一片,高大的府门,熟悉的石狮,都覆着厚厚的积雪。
她穿着一身簇新绣着缠枝梅花的大红羽缎斗篷,手里抱着一个暖烘烘的鎏金手炉,站在谢府巍峨的门楼下,看着祖父谢雍的马车在仆役的簇拥下缓缓驶离,车轮碾过积雪,出“吱嘎”的声响。
“祖父……”
她想喊,出的却是带着浓重鼻音的童声。
哦,对了,她好像……才六岁。
快过年了,祖父有急事要去南边一趟,不能带她,边把她送回了陈郡。
继母说,女孩子家总该学些规矩道理,便让阿爹把她送进了谢家的族学,跟那些兄弟们一道听学。
学堂里很冷,炭火不足。
先生讲的《千字文》对她来说太过简单。
第一次旬考,她答得又快又好,被先生当众夸赞,得了个头名,拿回一朵精致的绢花做奖赏。
她很高兴,可王氏生的儿子,她同父异母的弟弟谢充只考了第二。
谢充比她小一岁,是王氏的宝贝疙瘩。
他当场就摔了笔,哭闹起来,说姐姐抢了他的风头。
王氏心疼得什么似的,抱着他去寻了父亲谢翰之。
然后……然后她就跪在了祠堂冰冷的青砖地上。
谢翰之捻着胡须:“女子无才便是德。你弟弟尚未显露,你便急于争先,是谓不悌。锋芒过露,非福家之道。跪两个时辰,静静心。”
她攥紧了小拳头,仰着头,不服气:“父亲,先生说学无先后,达者为先。韫仪没有错。”
“还敢顶嘴?”谢翰之眉头一皱,“再加一个时辰。”
膝盖很疼,青砖很冷。
祠堂里只有长明灯幽暗的光,映照着祖宗牌位,森严肃穆。
她咬着唇,不让自己哭出来。
祖父南下是有要紧事,阿姐已经入宫,没人能帮她。
跪足了三个时辰,被嬷嬷扶起来时,腿都不是自己的了。
她一瘸一拐地回到自己住的院子,想着谢翰之、王氏还有谢充三人其乐融融的样子,心里忽然冒出一个疯狂的念头:她要去找阿娘!
她偷偷藏在书房画像里,温柔笑着的,据说出身江南书香门第、才情容貌冠绝一时的……亲生娘亲。
谢充有阿娘,她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