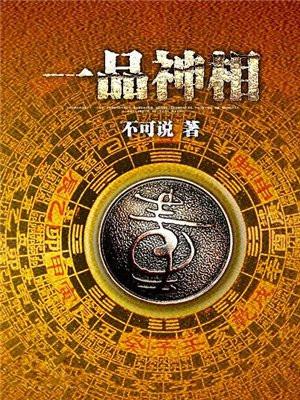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恢复视力后,发现夫君换人了 > 第十四章 你已经冷落我好久了(第2页)
第十四章 你已经冷落我好久了(第2页)
苏砚笑了笑,合上折扇:“夫人爽快。香,可以给夫人。分文不取。”
谢韫仪眉心微蹙:“哦?苏先生如此大方?”
苏研笑道:“听闻夫人是为了游园宴如此尽心,苏某岂能因一己之念,让夫人为难?这迦南香,便算是苏某预祝夫人宴席圆满的一点心意罢。”
“无功不受禄,如此贵重之物,不该白拿。”
青黛将一枚玉匣放到桌上。
“苏先生是奇珍阁的东家,想必遍览奇珍,我有一对前朝官窑的雨过天青釉双耳瓶,釉色莹润,器形古雅,或可入先生之眼,用以交换此香,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苏砚心痒难耐。
他爱好文玩字画,对谢韫仪口中的器物更是寻觅已久,瞥了一眼屏风后,他道:“夫人既然坚持,苏某便却之不恭了,明日,我让人将香送至府上。”
“多谢苏先生,今日多有叨扰,告辞。”
谢韫仪不是没有看到苏研瞥向屏风的那一眼,但是她不敢去看,万一屏风后的人真是江敛,暴露了她恢复视力的事,于她有大麻烦。
“夫人慢走。”苏砚亲自送至门口,这才转身回到书房。
江敛已从屏风后走出,负手立于窗边,神色莫辨。
“江兄,等她眼睛真的好了,看到这一切,看到你……你待如何?”
江敛沉默良久,最终只低低吐出两个字:“不知。”
他不知。
因着这一插曲,二人草草结束了对弈,直到夜色深沉,江敛才回府。
他推开门,见谢韫仪已然卸了钗环,长披散,只着素白中衣,独自坐在窗边的软榻上。
窗户开着半扇,夜风拂入,不知在想些什么。
江敛已沐浴过,换了一身月白色的绸缎寝衣,墨微湿,随意披散在肩头,那张过分俊美的脸,在昏黄烛光下,显出一种近乎妖异的美。
他手中端着一只白玉小碗,碗中热气袅袅,是熟悉的安神汤药气。
“怎么还坐着吹风?”
他走到她身边,很自然地伸出手,掌心贴上她的额头,又很快移开,皱了皱眉,“手这么凉。可是今日出去累着了,还是心里存了事,睡不着?”
谢韫仪微微侧开脸,低声道:“没有,只是白日睡多了,有些乏,却又不困。夫君怎么还未歇息?”
“你不在,如何歇息?”
江敛在她身侧的榻沿坐下,他没有像往常那样直接喂她喝药,反而伸手挑起她颊边一缕散落的丝,别到耳后。
他的目光落在她低垂的眉眼上,眸色渐深,忽然低低叹了口气。
“般般,”他唤她,“你心里,如今是不是只剩下游园宴了?”
谢韫仪一怔,下意识眨了眨眼。
江敛的指尖沿着她的耳廓,滑落到她的下颌,轻轻托起。
他那双总是深沉难测的眼眸里,此刻清晰地映出跳跃的烛火,也映出她茫然无措的神情。
“为了那宴席,你亲自出门奔波,与沈寻鹤周旋,今日又见了旁人。”
他语气里的酸意几乎要溢出来:“回来后,对着那香料、菜单,能琢磨上几个时辰。同我说话,也总是三句不离宴席。”
他倾身,凑得更近,温热的气息拂过她的脸颊。
“我的般般,”他几乎是贴着她的耳廓,用气音低语,那声音里混合着引诱:“你已经……冷落我好久好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