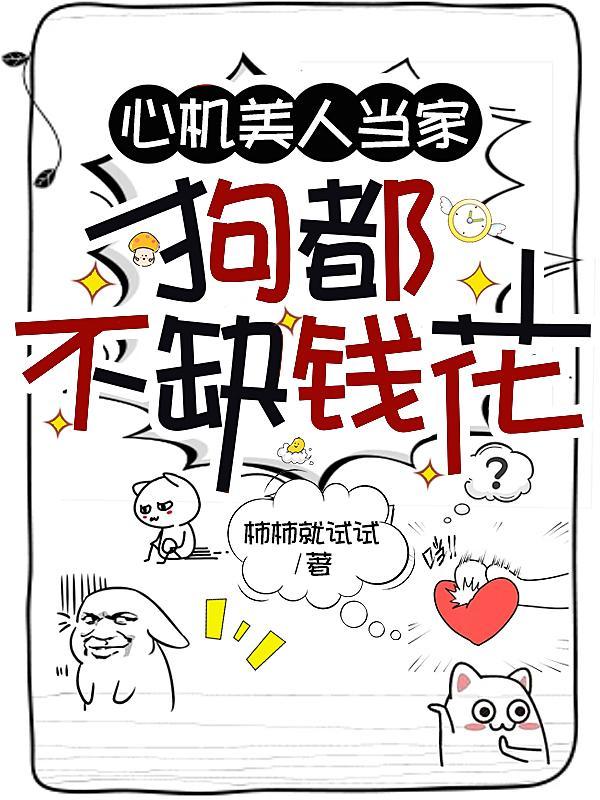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揽韫玉 > 第106章(第1页)
第106章(第1页)
他的声音粗粝沙哑,却传得很远,身后众人也跟着跪下,垂首不语。
很快,消息传到帅帐,谢瑾渊与温韫玉对视一眼。
“终于来了。”谢瑾渊语气平静,“带他们到外围军帐,本王稍后便去,多派些人小心戒备。”
当谢瑾渊来到那座临时用来会面的军帐时,赵铁柱等人已被允许进入,但依旧被隔在帐中一侧,周围是明显精锐的侍卫。他们面前放着清水,却无人去动。
见谢瑾渊进来,赵铁柱等人又是一礼,头埋得更低。
“不必多礼。”谢瑾渊在主位坐下,目光平静地扫过这群形容枯槁、却眼神执拗的“逆贼”,“赵头领此时前来,所为何事?”
赵铁柱抬起头,直视谢瑾渊,眼中没有了之前的阴鸷,只剩下一种近乎卑微的恳求与孤注一掷,“王爷!草民等……原是活不下去的百姓,被贪官污吏所逼才铸成大错,杀官夺粮对抗朝廷,自知罪孽深重,死不足惜!”
他话锋一转,声音带上了哽咽,“可……可山谷里的弟兄们,还有跟着我们的老弱妇孺他们大多是无辜的,如今瘟病横行,山谷已成死地,缺医少药,每日都有人死去……草民等人死便死了,可那些老人孩子,还有染了病奄奄一息的弟兄……他们不该就这么烂死在山沟里!”
他猛地以头叩地,发出沉闷的声响,“王爷!我们打听过了,知道王爷仁义,有神医有药,真的能救人,草民等不敢求王爷宽恕我们的罪过,只求王爷发发慈悲,救救山谷里那些还没死的人,给他们一条活路!
只要王爷肯救他们,草民赵铁柱这条命,还有这些还能动弹的弟兄,任凭王爷处置,要杀要剐,绝无怨言!”
说完,他伏地不起,身后众人也跟着磕头,寂静的军帐中,只听得见粗重的呼吸和压抑的啜泣。
谢瑾渊沉默地看着他们,这些人的投诚与其说是归顺,不如说是走投无路下为了给同伴争取一线生机而做的最后挣扎。
温韫玉站在谢瑾渊身侧,低声耳语,“王爷,这些人虽是反贼但情有可原,且熟知本地或可一用,眼下正是用人之际,救人之时,若能将他们纳入掌控既可彰显王爷仁德,安抚地方,也可补充人力彻底瓦解这股叛军残部。”
谢瑾渊微微颔首,他看向赵铁柱,缓缓开口,声音不高,却带着威严。
“赵铁柱,你等聚众造反,杀官夺城,按律当诛九族。”
赵铁柱等人身体一颤,头埋得更低。
“然,”谢瑾渊话锋一转,“念尔等亦是受贪官逼迫,走投无路下的选择。”
他站起身,走到赵铁柱面前,“山谷中染病百姓,本王自会派人前去救治,一视同仁,至于你等……”
赵铁柱猛地抬头,眼中爆发出难以置信的希望光芒。
“死罪可暂免,活罪难逃。”谢瑾渊语气转冷,“即日起,你等所有人需遵从本王军令,协助救治安置灾民戴罪立功,若有异心或再行不法,两罪并罚,立斩不赦!你可能做到?”
赵铁柱几乎要喜极而泣,再次重重叩首,声音颤抖却无比坚定,“能!草民能做到!。”
“谢王爷不杀之恩!谢王爷救命之恩!我等必效死力,绝无二心!”
流言蜚语
京城·御书房
空气凝滞得仿佛能滴出水来,殿内侍立的太监宫女个个屏息垂首,恨不得将自己缩进地缝里,唯恐被那御座之上散发的滔天怒意所波及。
皇帝手中捏着一份密报,指节因用力而泛白,手背青筋根根暴起。
他脸色铁青,胸膛剧烈起伏,眼中燃烧着骇人的怒火与一丝难以置信的惊怒。
失败了!
派去南境执行秘密任务的心腹精锐,竟然失败了!
不仅未能趁乱除掉谢瑾渊,反而折损大半,连个确切的消息都没能传回,只余零星的人带回了“计划暴露,遭遇伏击”的含糊回报。
“废物!一群废物!”皇帝猛地将密报狠狠摔在地上,犹不解恨,又一脚踹翻了御案旁珍贵的珐琅彩瓶,碎裂声在寂静的大殿中格外刺耳。
“朕养你们何用?!连这点事都办不好!谢瑾渊……谢瑾渊!你当真是朕的克星吗?瘟病都收不了你?!”
他来回踱步,如同困兽,心中除了愤怒,更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恐慌。
南境局势显然已彻底脱离掌控,谢瑾渊不仅没死,似乎还稳住了局面?连派去的杀手都铩羽而归……他到底在南境做了什么?
“陛下息怒,保重龙体啊!”福公公颤声劝道,额头冷汗涔涔。
“息怒?你让朕如何息怒?!”皇帝咆哮,“南境如今成了他谢瑾渊的南境,朕的旨意成了废纸,朕派去的人成了笑话!你告诉朕,接下来该怎么办?等着他谢瑾渊养精蓄锐,收拢人心,然后带着手里的兵马来清君侧吗?!”
就在皇帝暴怒未息,心腹们战战兢兢之际,一个更坏的消息,如同附骨之蛆,悄然从宫墙之外,市井之中以惊人的速度蔓延开来。
起初只是茶馆酒肆里的窃窃私语,很快便成了街头巷尾难以抑制的议论,最终化为汹涌的暗流,冲击着京城的每一个角落。
“听说了吗?南境那边……根本不是乱民造反那么简单!”
“何止啊,我有个远房表亲刚从南边逃难过来,说那边起了大瘟,死了好多人!”
“死人多不算什么,关键是朝廷……朝廷根本不管啊!”
“岂止不管,我听说,朝廷不但没派多少太医和药材,反而……反而派人去想把染病的将士和百姓,连同那些乱民一起……烧了灭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