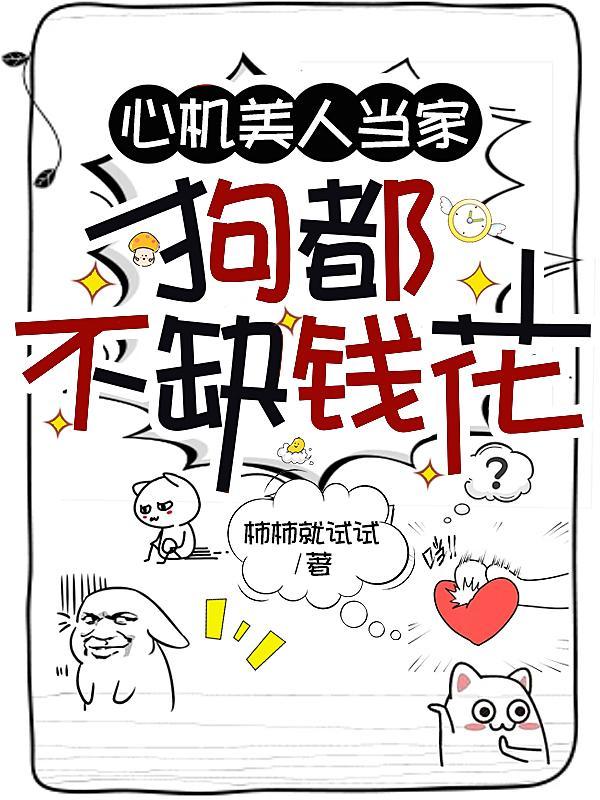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穿越到五代十国当女帝 > 第241章 暗棋布局(第2页)
第241章 暗棋布局(第2页)
而成德军经过安重荣之乱和契丹洗劫,正是这样一个“坑”。把杜重威挪到镇州去当节度使,名升实降,既酬其“功”,又解了近在咫尺的威胁。
他到了镇州,面对的是一个烂摊子,需要时间精力去收拾,短时间内难以形成新的威胁。
那么,空出来的义武节度使由谁来接任?这个地方太关键了,必须放一个至少目前看来更听话、更有掌控可能的人。
马全节,就是她物色的人选。用他替换杜重威,一石二鸟。
‘不过成德听起来就像要造反的样子,就改镇州为恒州,成德军为顺国军。’
她甚至想到了更深的层面。“成德”二字,在藩镇割据的背景下,本身就带有强烈的独立和叛逆色彩,如唐代成德节度使长期割据。
借这次平叛和节度使更迭的机会,改地名、改军号,既有“去逆化”、彰显朝廷权威的象征意义,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其历史上的“反骨”印记,赋予新的政治内涵。恒州,顺国军,听起来就“温顺”多了。
当然,这一切都还只是她脑海中的蓝图。杜重威是否会乖乖接受调动?马全节是否真如她所料的“可靠”且有能力镇守义武?其他藩镇,尤其是刘知远,对此会有何反应?都是未知数。
‘不过这些都得等马全节进京的时候再看了。毕竟历史上还有李金全引淮兵作乱,现在没有生,现在再生这个大晋就真的遭不住了。’
想到“李金全引淮兵作乱”这个潜在的历史事件节点,石素月心头又是一紧。现在南北叛乱刚平,国力空虚,债台高筑,若此时南方的淮河流域的南唐方向再出大乱子,与残存的安从进势力或其他心怀叵测者勾结,那真是雪上加霜,这个本就脆弱的朝廷可能真的会瞬间崩塌。
马全节原本的历史轨迹是平定了李金全之乱。现在,自己提前召他入京,准备调任,会不会反而破坏了某种“历史惯性”,导致李金全之乱无人遏制,提前或更猛烈地爆?
亦或是,将他放到更关键的义武军位置上,能更好地威慑四方,连潜在的南方叛乱也因此不敢轻举妄动?
她不知道。历史的河流在这里已经因为她这个“穿越者”的干预而改道,前方是更平缓的流域,还是更凶险的瀑布,无人能预知。她只能凭借有限的信息和对人性、时局的判断,小心翼翼地落子。
“唉……”
一声悠长而疲惫的叹息,终于从她唇间逸出,在空旷的殿内显得格外清晰。
“先等马全节入京吧。”她仿佛是对石雪和石绿宛说,又像是自言自语,“许多事情,急不来,也……想不全。”
她摆了摆手,示意她们可以退下处理诏令事宜。石雪和石绿宛虽然仍未完全明白公主的全部意图,但见其神色疲惫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便不敢再多问,躬身行礼,捧着那份刚刚写就、墨迹未干的诏书,轻步退出了大殿。
殿门开合,带入一股凛冽的寒气,很快又被殿内的暖意吞噬。
石素月独自留在偌大的宫殿里,炭火噼啪,铜漏滴答,更衬得一片死寂。她再次望向那份地图,目光在“安州”、“定州”、“镇州”也就是即将改名为恒州之间逡巡,手指虚虚划动,仿佛在推演着一盘看不见的、以天下为棋局的险棋。
马全节,会是她走对的一步棋吗?还是会在未来某个时刻,变成另一颗不受控制的炸弹?
杜重威,这只狡猾的狐狸,会甘心离开经营多年的巢穴,跳进那个看似华丽、实则破败的新坑吗?
刘知远,那头蛰伏在晋阳的猛虎,会对她这番调动,做出何种解读?是会感到威胁,还是更加轻蔑?
还有那三百五十万两……契丹的使节何时会到?朝中对此又会掀起怎样的波澜?桑维翰他们,能稳住局面吗?
无数的问题,像冰冷的蛛网,缠绕着她的思绪。她知道,自己不能停下来,不能示弱,更不能出错。
一步错,可能就是满盘皆输,不仅输掉权力,更可能输掉性命,输掉这个刚刚看到一丝喘息之机的国家。
她拿起旁边一份已经写好的、关于犒赏南线将士的草案,强迫自己将注意力转移到具体的政务上来。
窗外,夜色如墨,北风呼啸,卷起宫墙上的积雪,簌簌作响。漫长的寒冬才刚刚开始,而权力的博弈与生存的挣扎,亦在这深深的宫阙之中,无声而激烈地继续着。
石素月知道,她刚刚派出的,或许不仅仅是一道召见诏书,更是投向这潭深水的一颗石子,涟漪将起,波澜难测。
她只能,也必须,握紧手中的笔,看清眼前的局,在这条布满荆棘的孤路上,继续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