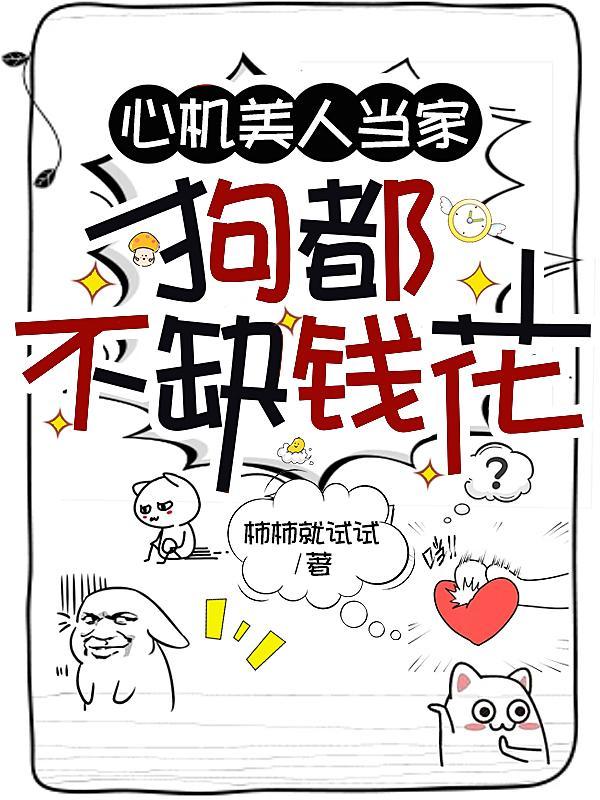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穿越到五代十国当女帝 > 第241章 暗棋布局(第1页)
第241章 暗棋布局(第1页)
汴梁的冬日,天色总是沉郁得早。宫灯次第亮起,在垂拱殿紧闭的窗棂上投下昏黄摇曳的光影,却驱不散殿内那股混杂着炭火微温与陈墨气息的凝重。
石素月独坐于宽大的御案之后,案头堆积的奏章已处理大半,却在她心头压下了更多无形而沉重的思虑。
她揉了揉因长时间执笔而酸痛的手腕,目光落在殿角铜漏缓缓滴落的水珠上。时间,像这漏中之水,看似沉静,却一刻不停地向前,带着不容抗拒的紧迫感。
河北的疮痍需要抚平,南线的“大捷”需要善后,契丹的三百五十万两债务如鲠在喉,朝廷内部看似平静的水面下,不知藏着多少漩涡暗流。
而最让她夜不能寐的,是那些手握重兵、散落四方的节度使们。刘知远在河东按兵不动,是福是祸?
杜重威此次“勤王”有功,但此人鼠两端,其心难测,两万义武军盘踞在定州,距离汴梁不过数日之遥,犹如卧榻之侧的一头随时可能反噬的饿狼。
成德军经此一乱,精锐尽丧,府库被劫,已近空壳,但地理位置紧要,绝不可轻易委于不可靠之人。
她的指尖无意识地划过一份摊开的、标注着各镇兵力与位置的简图,最终停在“安州”二字上。
安州,地处山南东道东北边缘,并非强藩,节度使马全节的名字,在当今诸多骄兵悍将之中,显得颇为低调,甚至……有些不起眼。
石素月沉吟片刻,终于提起了那支紫毫笔。她没有立刻蘸墨,而是先闭目凝神,将脑海中属于“后世”的、混杂而片段的历史记忆努力梳理。
马全节……这个名字,在正史记载中,确实没有留下太多浓墨重彩的篇章,他并非那种开基立业、叱咤风云的人物。
但是,她依稀记得,在某个时间点上,当安州附近的州县生叛乱,具体好像是……一个叫李金全的将领据州投靠南方的南唐时,正是这个马全节,迅而有效地出兵平定了叛乱,稳住了局势。
这说明什么?说明此人至少具备几个特质:其一,对朝廷大体忠诚,在关键时刻靠得住,不会轻易随波逐流或拥兵自重;其二,具备一定的军事指挥和应变能力,能够迅处理突危机;其三,或许正因为其“低调”和“不起眼”,反而少了许多跋扈藩镇的恶习,更容易被中央掌控。
一个念头,如同冰层下悄然游动的鱼,逐渐清晰起来。
她蘸饱浓墨,铺开一道空白黄麻诏敕,以沉稳端凝的笔触,开始书写:
“敕:安州节度使、检校太保马全节。本宫绍承丕绪,监抚万方,念将士之勤劳,思藩垣之重寄。今者,北疆初靖,南鄙敉平,乃眷忠勤,宜加召奖。卿夙着勋庸,久镇南服,军政修明,民庶安辑。特敕卿即日整备,克期赴阙陛见,本宫将面谕机宜,别有委任。沿途州府,妥为接待,不得延误。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写罢,她仔细看了看,吩咐道:“用印,往安州,六百里加急。”
一直侍立在旁的石雪上前,小心翼翼地用上监国公主宝印,又加盖了政事堂的印信。石绿宛则迅将诏书内容誊录于留底簿册。但两人眼中,都掩不住一丝困惑。
终于,石绿宛忍不住,趁着石雪封装诏书的间隙,轻声问道:“殿下,安州马节帅……此次南线平叛,似乎并非主力,功绩亦不显赫。如今南北皆平,正是论功行赏、稳定人心之时,突然急召其入京……婢子愚钝,不知殿下深意何在?”
石雪虽然没问,但封好诏书后,也投来询问的目光。她们跟随石素月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政变、屈辱的借兵、惨烈的平叛,对公主的决断素来信服,但这一次的调动,确实有些突兀,甚至显得有些……“小题大做”。
马全节的名声和实力,在众多节度使中实在排不上号。
石素月没有立刻回答,她靠回椅背,目光再次变得幽深,仿佛穿透了宫殿厚重的墙壁,看到了更远的地方,以及……更久以后可能生的变故。
‘马全节在历史上存在感不是很高,但在历史上时李金全据州叛,马全节能够平定,说明他也有一定能力……’
她在心中默念着这个判断。乱世之中,忠诚与可靠,有时比赫赫战功更为难得。刘知远有能力,但野心勃勃;杜重威有点小聪明,但毫无节操;高行周资历老、实力尚可,但身处洛阳,牵一而动全身,且其态度也需要进一步观察。
相比之下,马全节这种有一定能力、背景相对单纯、目前看来对朝廷命令执行度较高的将领,正是她现在急需的“棋子”。
‘这一次考虑是为了让马全节去担任义武节度使,杜重威如果再待在那里,我可不觉得他能听我的命令了……’
这才是她真正的盘算。杜重威这次出兵,虽有斩获,但其观望、抢功的嘴脸暴露无遗。
两万义武军留在他手里,驻扎在京畿北面咽喉之地,就像一根刺,扎得她寝食难安。
必须把他调走!调到一个看似重要、实则已被掏空、且远离汴梁核心区域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