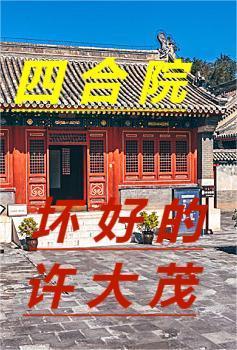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戏精女官升职记 > 第47章 通敌(第2页)
第47章 通敌(第2页)
一旦截获了粮草,西陵人就是小水洼里头的鱼,翻不出多大浪花来。
“程轼轻敌,”宋容暄唇边勾出一抹故作轻松的笑,“他与燕绍向来不和,又急着在女帝那儿邀宠,只要我们佯攻女帝,程轼和燕绍必定来救,届时与西门东门的守军前后夹击,西门东门的敌军就可以被解决一部分。”
“那南门的压力可就太大了,”魏司归急得直搓手,“本来城防就已经快崩溃了,万一再……”
“南门是严老将军亲自守城,”宋容暄阖了眼休息了一会,道,“只要城中还有人,他就不会退。”
别的城门,他还真没有这个把握。
明晃晃的日光洒在飞檐屋顶,金线划开一道优美的弧度,落在了皇上的案几上。
钱桓和骆清宴一前一后到了明德殿,皇上正在批奏折,殿内安静得落针可闻。
“陛下,二殿下和钱指挥到了。”卢公公捏着嗓子道。
“让他们进来吧。”骆奕把笔一摔,颇有些郁闷。
他知道这都是因为边关战火的缘故,边关捷报一日不来,他一日不得安枕。
不料这二位当真是来给他添堵的。
二人给骆奕行礼后,骆奕慢悠悠地啜了口茶,问:“什么事?”
“下官去天牢提审,不料正碰见二殿下私放人犯,企图偷梁换柱,假公济私,罔顾国法!”钱桓可算是小人得志了,一副胜券稳操的模样。
“允宁,可有此事?”
“回父皇,儿臣见阿盈高热不退,狱卒又罔顾人命,这才不得已出此下策,让阿盈到我府中诊治,太医院的闻太医可以为儿臣作证。”骆清宴说话不疾不徐,他在来的路上已经编好了说辞,自然不会甘愿任人宰割。
“陛下,二殿下分明是信口雌黄,企图脱罪!”钱桓铜铃一般的眼珠滴溜溜转,几乎要瞪出来了。
“钱副使诬陷本王,不也空口无凭吗?”骆清宴冷冷一瞥,钱桓的气势顿时矮了半截。
“若说凭据……”钱桓抖抖袖袍,从怀中掏出一个信封,“请皇上过目!”
卢公公连忙恭敬地递了上去。
骆清宴尚且不知道钱桓葫芦里埋的什么药,料想他也掀不出什么浪花来,刚要反唇相讥,不料余光瞥见骆奕的脸色,顿时心下一惊。
只见骆奕咬牙切齿,脸上肌肉剧烈地抖动着,骆清宴已经很少看见他如此愤怒的表情了,帝王,向来都是不喜形于色的。
这是摊上了多大的麻烦?
骆清宴瞧见钱桓慢条斯理地捋起胡子来,更是如同头顶上悬着利剑一般坐立难安。
那剑随时可能落下。
过了不过一盏茶功夫,骆奕把信扔到了骆清宴脚边,声音如同惊雷在他耳边炸响,“你自己看!”
骆清宴捡起来,从头到尾读了一遍:
自入枢垣,每见太仓积粟如山,库银映目,常思将军帐前风雪苦寒。今上昏聩,宰辅贪墨成风,正可借势渔利。妾虽女流,愿效犬马,已结纳仓场官吏十数人,暗改漕粮簿册,虚增损耗,岁吞米粮二十万石、白银三十万贯。
然转运非易,须假官船之便,借商队之形。恳将军遣心腹,以互市为名,于江陵渡口接应。所筹钱粮暂藏盐商别院,待南风起时,便可扬帆南下。事成之后,望将军践诺,许妾金屋藏娇,永避此浊世牢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