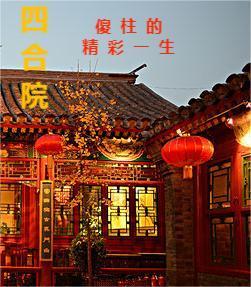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权臣西门庆,篡位在红楼 > 第210章 桂姐金莲嗲求老爷常峙节三借钱(第2页)
第210章 桂姐金莲嗲求老爷常峙节三借钱(第2页)
吴月娘何曾见过这等景象?
她虽是内宅主妇,到底出身正经人家,最多只听过些后宅阴私,哪里懂得风月场中这些伺候权贵的惨样?
直被眼前这一片狼藉的皮肉惊得倒抽一口冷气,脸都白了!
她下意识地用帕子掩住嘴,脱口而出:「哎——哎哟!作孽啊!——不过——不过好在他——他是个去了势的——身子不全的人——」
安慰道:「没真个被他占了身子去——这皮肉之苦,养养也就好了——」
吴银儿苦笑:「奴家倒宁愿他真个占了身子去!横竖——横竖不过是一闭眼、
一咬牙的事儿!哪似这般——这般钝刀子割肉、活活受这零碎的酷刑?那滋味真真是——生不如死啊!」
吴月娘张了张嘴,不知该如何接话,只能保证:「你且宽心——今日那薛公公是断断不会来的——」
再说这常峙节挨到第三冬日头上,那真个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囊中如洗,莫说过冬,便是眼前这单间的破屋漏户,也立时三刻要被那房东赶将出来。
万般无奈,只得厚著面皮,一步三挪,寻到应伯爵那所在。
虽是个略略整齐的小院,却也透著几分寒酸。
报了小厮推门进去,厅内屋里炭火半死不活,一股冷气直钻骨缝。
那应伯爵裹著件油光水滑的半旧羊皮袄子,正歪在热炕头上,跷著脚,「咔吧咔吧」地嗑著瓜子儿,脚下已吐了一小堆皮儿。
见常峙节缩著脖子,一脸苦相蹭进来,应伯爵眼皮子懒懒一撩,慢吞吞支起身子,嘴里却先热络起来:「哟嗬!老七!今日是哪阵仙风把你吹到我这穷庙里来了?快坐!快坐!」
嘴上这般说,身子却纹丝不动,只伸出脚尖,把那炕沿下一个落满灰的矮板凳,「哧溜」一声勾到常峙节跟前。
常峙节冻得两手通红,不住地搓著,半边屁股虚虚挨著那冰凉板凳坐下,也顾不得寒暄客套,喉咙里「咕噜」几声,脸上挤出个比哭还难看的笑,期期艾艾道:「应——应二哥——兄弟实在是到了那阎王殿前,没奈何了——家中灶冷锅空,房东催租,逼得如同索命——眼看就要扫地出门——万望二哥念在往日情分,挪借五六两银子与兄弟——好歹——好歹应过眼前这刀山火海——」
应伯爵听罢,把嘴里的瓜子皮「噗」地一声吐在地上,长叹一口气,脸上立刻堆起十二分的愁苦,拍著自己肚皮道:「哎呀我的老七!你这话可忒生分了!
咱们兄弟一场,原该周济!只是——」
他话头一转,眉头锁得更紧,「不瞒你说,兄弟我这几日也是精光溜滑,外头瞧著光鲜,内里早空了!咬著牙,勒紧裤带,还能替你抠搜出一两的散碎银子救急。可你要借五六两?」
他像是被剜了心头肉:「哎哟哟!这岂不是要掏我的心肝五脏么?实在是——
实在是力不从心,有心无力啊!」
嘴里说著,那双眼睛却滴溜溜在常峙节瞬间垮塌、灰败如土的脸上打了个转,忽地一拍脑门,故作惊诧道:「咦?我说老七!你也是糊涂!放著西门大官人那尊真佛你不去拜,倒来我这座破庙烧香?那西门大爹是何等富贵?手指缝里漏下一点金末子,也够你一家子吃用不尽,穿金戴银了!何苦来我这里打饥荒?」
常峙节一听「西门」二字,那脸越灰败。
他重重地叹了口气,声音低得如同蚊蚋哼哼:「唉——应二哥——快——快别提了——兄弟我——我前日里、昨日里,腆著老脸,连著两趟——寻到那西门府高门大户前——」
「哦?如何?」应伯爵猛地直起腰,两眼瞪得溜圆,活像听见了海外奇谈,抢著说道:「西门哥哥他必定是二话不说,立时就应承了!」
常峙节缓缓摇著头,嘴角扯动,露出一个比黄连还苦的笑容,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兄弟我——门都没迈进去一步——」
「甚么?!」应伯爵像被针扎了屁股,「腾」地挺直了腰板,眼珠子瞪得牛蛋也似「不能吧?!常老七,你莫要嚼蛆哄我!西门大爹是何等样体面人物?最是念旧情、讲义气的!咱们这些老兄弟,他哪回不是抬举照拂?」
「。。。是真格儿的。。。」常峙节喉头干咽了一下,嗓子眼紧,挤出几个字:「应二哥。。.此一时。。。彼一时了。。。西门哥哥如今何等贵人,府里进出的,不是戴纱帽的文官老爷,就是挎腰刀的武官老爷,便是宫里穿蟒衣的内相公公,那也是脚不沾地儿的常客。。。我这等。。。算个甚么。。。」
应伯爵脸上那笃笃定定的笑容唰地冻住了,眉头拧成了个死疙瘩。
正这当口,一个小厮颠儿颠儿跑进来,递上一张名帖:「二爷,外头有个湖州来的客商何官人求见。」
那何官人急火火进来,团团作了个揖,道是手里压著上千两上好的湖丝在码头刚卸下货,本要赶往京城,可家中出了急事,等著银子使唤。
听闻应二爷是清河县头一号路路通的帮闲,求他千万寻个买家,立时三刻出手!原价一千两的货,只消七百两就咬牙抛了!
应伯爵眼珠儿滴溜一转:「何官人放心!包在应二身上!这等便宜好货,还怕寻不著识货的主儿?不过嘛。。。」
他话音一顿,两根指头搓了搓,嘿嘿一笑:「咱们这行规矩,二十两银子的「鞋袜跑腿钱」。。。官人您看。。。?」
那湖商正急得火上房,一听这话,忙不迭点头哈腰:「使得!使得!应爷辛苦,二十两就二十两!只要货能立时三刻脱手,小可绝无二话!」
应伯爵登时眉开眼笑:「痛快!何官人果真是个爽利人!你且宽心,少则一日,多则三日,管教你银子到手!」
待那湖商千恩万谢、脚不沾地地去了,应伯爵这才扭过头,脸上那点得意劲几还没褪尽,对著面如土色的常峙节咂咂嘴:「啧。。。常兄弟,我看哪。。。西门好哥哥。。。怕真不是那等凉薄之人。。。」
常峙节将他讨要鞋袜钱」的嘴脸看得分明,心口像被冰坨子塞住,苦著脸,长长叹了口气,声音又虚又飘:「应二哥。。。旁的也不说了。。。只求你。。。看在往日情分上。。。借给兄弟一两二钱银子。。。不拘多少。。。暂渡眼前这鬼门关。。。」
应伯爵眉头锁得更紧,捏著下巴,光咂嘴不吭声。
常峙节眼巴巴望著他,脸上那点灰白,彻底沉成了冰冷的死灰。
正这腌臜尴尬当口,忽听得院门外「噔噔噔」一阵急雨也似的脚步声,紧跟著一个喜鹊报春般的清亮嗓子直戳进来:「应二爷可在家么?!」
话音未落死,门帘子「哗啦」一挑,西门府上另一个得用的小厮平安,裹著一身崭崭新、油光水滑的青缎袄裤,头上暖帽压著眉梢,一溜风钻了进来。
「应二爷安好」眼梢子一溜,瞥见缩在炕沿边、灰头土脸的常峙节:「哟!
常七爷也在这儿?这可巧了!省得小的多跑一趟腿儿!」
平安笑嘻嘻地对常峙节道:「常七爷,小的正要往您府上去呢!我们大爹今日在府里摆下精致酒席,专程命小的来请应二爹和常七爷您二位并其他几位爷过去坐席!说是好好叙叙兄弟情谊!」
应伯爵一听,方才那点子疑云疑雨,「呼啦」一下,早被这阵暖风吹得无影无踪!脸上「腾」地绽开一朵大牡丹花也似的笑,仿佛凭空捡了个金元宝!
他「噌」地从炕上弹下来,蒲扇大手「啪啪」拍著常峙节瘦伶伶的肩胛骨:「瞧瞧!老七!我方才放的是甚么屁?!我就说西门哥哥是何等样念旧情、
讲义气的奢遮人物!如何?专席相请!还特意让平安来寻你!可见哥哥心里始终记挂著咱们呢!」
又朝著平安说到:「你且回报西门好哥哥,我们二人一起随后就到。」
见到平安应声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