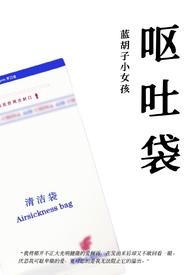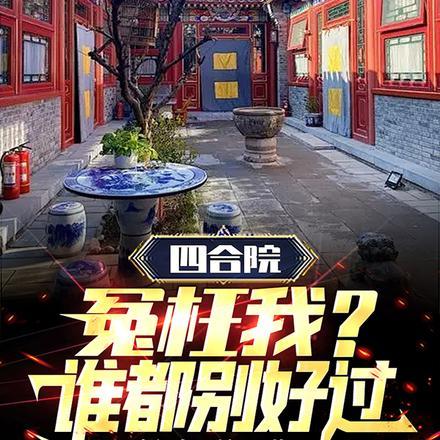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1848大清烧炭工 > 第291章 不老实的汉阳士绅(第1页)
第291章 不老实的汉阳士绅(第1页)
周汝诚来回踱步,思忖良久,说道:“咱们周家以养鱼贩鱼起家,为父养鱼的手艺也没落下,咱们家少要些田,多换些鱼塘。”
“听凭爹爹做主。”周家兄弟异口同声道。
周家向来是周汝诚做主,以往周家的日子能过得红红火火,也是靠周汝诚里外操持,他们对周汝诚的决定没有异议。
当然,两兄弟也清楚他们老爹的秉性,周汝诚向来强势,有异议他们也说不过周汝诚。
“你褡裢里装的是什么?粥棚的吃食?”周汝诚的目光落在周济鸿鼓囊囊的褡裢上,忍不住吞咽了口口水,满怀期待地问道。
“不是吃食。”周济鸿打开褡裢,露出褡裢的几本书。
“粥棚粥粮的圣兵知道我们家读过书,了这些书给我,让我们家闲时好生读书,说什么明年北王开科考试,会考这些书里头的内容。”
听到科考二字,周汝诚不禁眼前一亮。
他们周家家境有起色后,累世参加科举。
但江夏县科考竞争十分激烈,考了几代人,也只他爷爷中了个生员。
到了他儿子这一代,只有周济深中了童生,周济鸿则是花钱捐了个监生。
周汝诚信手拿起几本书略略翻了翻,看了几眼。
都是些关于舆地、算学、以及他不懂,带豆芽菜文字的书籍,书中也没有关于天父天兄的词句。
“先吃饭吧。”
周汝诚让周济鸿暂时先把书收起来,随即收拾了些散落在院子里的废木料来到没有铁锅的砖灶前生火。
周济鸿把书放回房间后,拿出从镇里粥棚领到的六个拳头大小的红薯,放进灶膛烤了起来。
待红薯烤得差不多了,周家父子一人拿着一根比筷子略粗的木棍往红薯里一扎,将红薯从滚烫的灶膛里取了出来。
趁着凉红薯的功夫,周汝诚神采奕奕地向两个儿子讲述周家祖宗家的往事。
周家祖宗的事迹在周家世代相传,每个周家家主都将祖宗的事迹挂在耳边。
周济鸿、周济深以前没少听周汝诚说祖宗家的经历,早听得他们耳朵都起茧子了。
不过这回周济鸿、周济深两兄弟听得格外认真,丝毫没有像往日一般,父亲一说起这些就显露出不耐烦的神色。
因为他们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已一去难返了,不得不像他们祖宗那般,为生计而劳作奔波。
翌日清晨,周汝诚带着两个儿子,去见江夏清田队,向负责分田的图正表明他们家只要六亩中则水田,剩下的田额,全部都换成鱼塘。
负责东湖镇均分田地的是江夏清队二组图正王旭焘。
面对周汝诚提出的要求,王旭焘颇为意外,好奇地问道:“别家巴不得多要田,少要山塘芦地,你们家是头一家少要田,多要鱼塘的。”
王旭焘一旁的弓手陶振永提醒道:“养鱼可没种地安稳,没个三年打底,难见收益,你可想好了?一旦登籍造册,不能反悔。”
“禀上官,草民想好了,绝不反悔,草民家祖上就是养鱼卖鱼的,圣朝雅政,给小民田地,往后大家伙的日子肯定过得红红火火,大伙日子红火了,就能吃上荤腥,届时草民的鱼正好长成,只怕是没出东湖镇,就被人买光了。”周汝诚忙不迭说道。
“你说话倒是中听。”
王旭焘埋翻阅着册子,同几个本组的组员交头接耳,计议了一番,计议毕,达成一致意见,王旭焘指着半里外的一处鱼塘对周汝诚说道。
“田螺坑附近有口好塘,大小正合适,只可惜鱼塘附近没有中则田,只有上则田,为便你们劳作,分你们家六亩二等上则水田,你可同意?”
周汝诚是本地人,清楚田螺坑附近田地的情况。
田螺坑附近的上等水田只要精心耕作,寻常年景产量都是两石半打底,而且能稻麦轮作,一年收两次粮。
只要他们父子三人手脚勤快,打理好这六亩上等水田,温饱肯定是没问题的。
再者,少打理些田,他也能腾出更多的精力在鱼塘上。等熬到鱼塘出鱼了,他们家的日子就好过多了。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周汝诚坚定地点点头,说道:“感谢上官照顾,草民同意。”
“既是如此,随我去插田插塘。”王旭焘合上册子,带着周汝诚插田插塘去了。
前去插田插塘的路上,周汝诚一面走,一面小心翼翼地询问道:“布告上说,分了田地后,江夏县业农之民,头年每人可领二石粗粮和种粮,给合二两银钱的安家费,农具也免费。这些东西何时领,又是到何处去领?”
周汝诚现在除了一套倾颓的宅子外一无所有,很关心布告上北殿承诺给江夏县业农之民放的钱粮农具会不会,什么时候。
“这些事情不归我们清田队管,农具和粮由你们东湖镇的农会,安家费由农会信用社,口粮若不够,可到农会开凭证,到农会信用社借粮,借粮一石年息半斗。具体什么时候,农会会有布告,我看你也是读书人,应当识字,平时留意着些。”王旭焘耐心地解答了周汝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