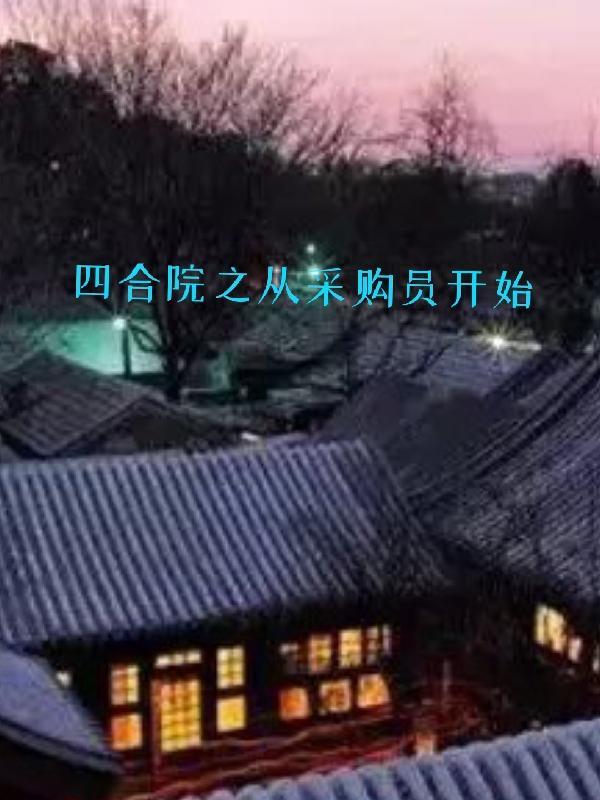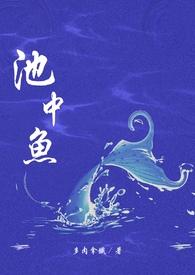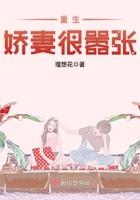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1848大清烧炭工 > 第290章 老实的江夏旧绅(第2页)
第290章 老实的江夏旧绅(第2页)
周家的女眷多在东殿女馆之中,没能一同逃离东殿,回到江夏县,目下生死未卜。
周家老二周济鸿来到驻防东湖镇圣兵开设的粥棚领了一袋红薯,顺道向粥棚的圣兵打听北殿对江夏县业农之民具体政策。
负责东湖镇粥棚的组长是湖南永州府人,举家加入北殿的时间不长也不短。
他们家前几天刚刚在白沙洲附近分到了三十几亩上好的沙洲地,心情极好,耐心地周济鸿解释了对江夏县本地务农者的政策。
周济鸿牢记于心,谢过粥棚的那名圣兵组长,临别时,这名圣兵组长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喊住他,塞给他一个装了书的褡裢,并嘱咐了一番,让他回去好生读这些书。
回到院墙倾颓、房屋坍塌,仅存两间偏房尚能勉强居住的周家宅院内。
回去的路上,周济鸿撞见了原来的打短工的同乡吴得柱。
吴得柱拉住他眉飞色舞地向他炫耀他们吴家分的就是原来周家的好地。
周济鸿又急又怒,举拳欲打。
当吴得柱说出他大儿子已经加入北殿,当了圣兵,周济鸿无可奈何地把刚刚举起的手收了回来。
步入院内,其父周汝诚和五弟周济深正在弯腰拾掇着一片狼藉的院子。
数月的奔波劳累,周汝诚早已瘦到脱相,连辫都变得斑白。
想到从安庆逃到黄梅县的一路上,父亲将或是乞讨,或是偷来的食物让给他们兄弟二人,自己时常饿着肚子,周济鸿鼻子不由得一酸。
背着褡裢的周济鸿向周汝诚走去:“爹爹,我回来了。”
“让你打听的事情,你都打听到了?”周汝诚暂时放下手中的活计,抬头问道。
“打听到了,咱们江夏县原来的业农之民,也按丁口分田地,每人分五亩中田,咱们家有三口人,能分到十五亩中田。”周济鸿愤愤不平道。
“咱们家隔壁原来农忙时常给咱们家打短工的吴得柱一家子,原来分地没有,分到了足足二十五亩田!
他们家分的田,都是咱们周家的田!刚才在路上撞见他,别提多嘚瑟了,还说他已经让大儿子报名参军当了圣兵,说他们家现在也是北殿的人了。”
周家原来有两顷半的田,五口鱼塘,在东湖镇还有间鱼铺,虽说和省垣武昌的大富大贵之家没法比,可也是殷实之家,衣食无忧。
看到原来自家的短工分的田比他们家多,还他娘的分的是他们家的田,周济鸿心里很不是滋味,气呼呼地补充说道。
“这田也不是那么好拿的,要剪了辫子才能拿田。爹爹,不然咱们跑吧,不受这鸟气!”
周济鸿话音刚落,周汝诚便甩了他一个耳刮子:“跑?!咱们现在除了这座宅子,分文不剩,口粮都是靠北殿接济,往哪里跑,又能去哪里?”
他们周家现在唯一的家当只剩脚下的这座宅院,连他们的吃的口粮,都要去北殿在东湖镇开设的粥棚领。
周家的田被分了出去,周汝诚心里又何尝没有情绪。
毕竟这是他们周家祖辈数代人积攒下来的家业。
换做是半年前,突然有造反武装把他们周家的家业分给泥腿子,周汝诚肯定不同意,会想方设法抗争。
但这半年多来,周家突遭厄难,周汝诚又遭遇了许多事情,遇事冷静了许多。
从坐拥两顷半的田产的殷实之家,到只能分得十五亩中田,落差固然很大,难以接受。
不过在东殿男馆中待了数月,侥幸逃回江夏县的周汝诚,只求一个安稳,希望两个儿子能够在这乱世活下来。
“我就是气不过!”周济鸿捂着被打得通红的左脸说道。
“爹爹,不然我也报名当圣兵吧,多少能给家里省点口粮,也能为家里挣个身份,不致被人欺负。”周济深想了想,说道。
“铳炮刀枪无眼,不许去!都给我在家里老实待着!”周汝诚厉声呵斥道,制止了周济深的这个念头,旋即偏头看向老二周济鸿,问道。
“布告上写的明年免纳粮,少要田可换些山塘,此事你可问过圣兵了?”
“问过了,确有此事。”周济鸿回答说道。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