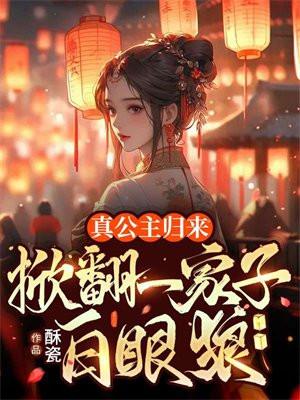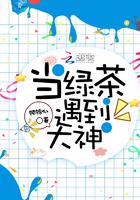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1848大清烧炭工 > 第276章 王无戏言已修改(第2页)
第276章 王无戏言已修改(第2页)
各殿已准备就绪,随杨秀清顺江而下,前往江南,也就这几天的事情。
等杨秀清他们一离开武昌,彭刚就可以将北殿军民进驻人去城空的武昌城,逐次分田给地予以妥善安置。
他给出的半个月的期限,都已经算是保守了。
得到肯定的答案,在场的湖南诸生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站在湖南诸生前头,踌躇不定的刘典,正欲开口询问彭刚什么时候,要给他们安排什么职务时。
彭刚却率先开口了:“素闻湖南士子重经世济民之学,不仅研读四书五经,还主动学习舆地、兵政、农学、水利等实用之学。只是不知尔等从书院学到了多少分真才实学,是否有辱左先生、王先生之名。”
此言一出,这些年轻气盛的湖南诸生沸腾开来,表现得很不服气。
不是所有的湖南读书人都有幸能够进入岳麓书院、城南书院这些知名书院就学。
能够有幸拜入左宗棠、王佺这等名师门下的读书人更是少数。
彭刚眼前的这些湖南诸生两样都占了,加上又都是年轻人,难免有些傲气。
“殿下觉得我等是在书院虚度光阴?”刘典第一个表示不服。
“殿下若是怀疑我等学艺不精,我可与殿下切磋一二!舆地、兵政、农学、水利任凭殿下挑选!”左宗棠的二舅子周诒晟自认为得了左宗棠的真传,是湖南排的上号的舆地大师,且于兵政、农学、水利等方面的学问也学得不错,表示要与彭刚切磋一番。
“殿下质疑我等可以,但还请殿下莫要看轻我们的先生。”王旭焘开口说道。
“汝充(周诒晟,字汝充),莫要自取其辱,殿下的学问,我在衡州府时便和殿下切磋过。殿下的著述,你们在柳庄又不是没看过。我平日里是怎么教你的,学海无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左宗棠白了周诒晟一眼,这话既是说给周诒晟听的,也是说给其他学生听的。
这是他的这些学生们第一次见彭刚,左宗棠不希望他的学生给彭刚留下不好的印象,以致被冷落乃至雪藏。
左宗棠的话音刚落,左宗棠的学生们纷纷闭口噤声,只有几名王佺的学生,仍旧在低声交头接耳。
“左先生曾在门下提笔写下过一副对联,上联为身无半亩,心忧天下。”彭刚陡然提高了说话的声量。
“我现在有武昌、汉阳之田数百万亩,不知诸位可有力清丈均分,造福治下军民。若诸位真有经世济民的本事傍身,我又何惜武昌、汉阳两府的官缺。
清廷给不了你们施展毕生所学的地方,我给!清廷给不了你们的官缺,我给!”
彭刚倒不是在给眼前的湖南诸生画饼。
等杨秀清他们撤走之后,武昌、汉阳、黄州、岳州府四府的部分州县,都是北殿的实控地区。
空缺的官职很多,光靠彭刚自己的那些学生,填不满这些地方的官缺。
彭刚的学生长于治军,哪怕是三期的学生,也是当做储备军官培养,行政方面的经验,则较为欠缺。
左宗棠、王佺的这些有不少给县官当过幕僚,或者在县里的六房任职过,管理地方的经验要更为丰富。
两者可以相互取长补短,相互摸索学习。
“此话当真?”湖南诸生们的眼中焕出灼灼焕彩,跃跃欲试。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既擅长写八股文,又精于多门实学的人终究是少数。
莫要说左宗棠的这些学生们,就连左宗棠本人也不擅长八股文,其师贺熙龄评价给左宗棠试卷的评语为:文虽佳,情不中程式。
左宗棠的举人功名,也不是通过常规的途经取得的。
左宗棠因父母相继去世需守孝,错过了获取生员资格的院试,通过“捐监”方式,向亲友筹借了一百零八两银子购买国子监监生资格(例监),以此绕过生员身份直接参加乡试。
道光帝五十寿辰的恩科。
若非廷特命主考官徐法绩复查所有遗卷,以防遗漏人才,副主考胡鉴突然暴病身亡,徐法绩被迫独自复审五千余份遗卷,从中补录六人。
又若非主考徐法绩偏好实务文章,且有时任湖南巡抚吴荣光为左宗棠背书担保,左宗棠的卷子难被认可,点为补录六人中的头名中举。
左宗棠能得中举人,自身的硬实力、人脉、运气,缺一不可。
不是每个人都有左宗棠这么过硬的实力、人脉、运气。
常规科考的晋升之途名额有限,捐官又不是这些多数生长于小门小户之家的湖南诸生有门路捐,能够捐的起的。
官缺对这些湖南诸生的吸引力很大。
若非有太平天国和北殿的变数,他们之中的多数人,实学学的再好,也难有用武之地,难逃潦草庸碌一生的命运。
“王无戏言!”彭刚的回应犹如掷地金声。
“愿参与田亩清丈均分,为我行《武昌府、汉阳县耕者有其地土地法令》,造福天下百姓的,皆可报名。我素来唯才是举,田亩清丈、均分的差事办得又快又妥帖的,择优授予官缺。”
“愿为北王殿下效力!”心潮澎湃的湖南诸生齐声回应表态道。
“好!尔等有此心,何愁打不回湖南桑梓地,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造福苍生,彪炳史册,光耀祖宗门楣!”彭刚高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