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五小说网>缱绻与决绝(杨幂、欧豪主演影视《生万物》原著) > §第七章(第3页)
§第七章(第3页)
听着这话,想想爹一辈子也实在可怜,大脚的泪便涌出了眼窝。
封二老汉又说:“爹没留下钱,没留下地,可是我还有该留下的东西。是啥呢?就是怎么打庄户,怎么种庄稼。这是我在地里扑腾了一辈子,一点一滴积攒在心里的。大脚,你说你要不要?”
大脚急忙点头:“要,要!”
老汉便抬眼瞅着上方,像是看着房顶,又像是将目光穿过房顶望着无垠的虚空。他说:“大脚,世上七十二行,咱是打庄户的。打庄户是干啥的呢?是侍弄地的,是种庄稼的。老辈人都说:十年读个探花,十年学不精庄稼。真是这样呵,打庄户真是不容易呵。”
“打庄户的第一条,你要好好地敬着地。庄稼百样巧,地是无价宝。田是根,地是本呀。你种地,不管这地是你自己的,还是人家的,你都要好好待它。俗话说:地是父母面,一天见三见。依我的意思,爹娘你也可以不敬,可你对地不能不敬。你别看它躺在坡上整天一声不吭,可是你的心思它都明白。你往地头上一站,你心里对它诚是不诚,亲是不亲,它都清清楚楚。你对它诚,对它亲,它就会在心里记着你,到时候用收成报答你。这是最要紧的事,一丝一毫也马虎不得!”
“这是敬地。除了敬,还要养。人不亏地皮,地皮才不亏肚皮。这是一笔账,明明白白。怎么养?一是精耕二是上粪。老辈人说;书要苦读,地要深耕。有使乏了的牛,没有耕乏了的地。地就是这么一件东西,你越是耕深了它越喜欢。一尺银,二尺金,深耕三尺聚宝盆。咱那几亩为啥长庄稼比一般人家的好?就因为年年耕得深。你也知道,咱家以前虽然只有一头驴,劲头小,可咱都是一道犁沟耕两遍的。等你以后添了地,无论如何也要一年深耕它两遍……再是上粪。人是饭力,地是粪力。马无夜草不肥,地无粪土不壮。这些理你也明白,我就不多说了。我要说的是,你在鳖顶上刚开出的地,粪力也太缺了,过几天,你把咱家院子刨一遍,把土送去。你别看这土不是粪,可是三年没起过的院心土,两车就能顶上一车粪。这事你可别忘了……”
“你知道怎样敬地,怎样养地了。我就再跟你说怎么样种庄稼。庄稼十八样,样样有门道。我先跟你说种麦……”接着,封二老汉便讲何时种麦最好,怎样换地茬,怎样选种,怎样下种,怎样施肥,怎样防止冬前旺长,怎样在年后锄草,怎样防黄疸,怎样防倒伏,怎样收,怎样打,怎样晒,怎样藏……讲得无微不至。见儿子连连点头听得认真,老汉情绪渐渐变好,黯淡了多日的酒糟鼻子又微微泛红。
讲完了种小麦,老汉又讲其他庄稼怎样种:谷子、糁子、芝麻、地瓜、秫秫、花生、玉米、荞麦、大麦、黄豆、绿豆、芝麻、棉花……
一样一样,从上午讲到下午,从下午讲到晚上。这期间,绣绣与婆婆端上了午饭,老汉不吃;端上了晚饭,老汉还是不吃。
虽然两顿饭没吃,可是老汉却一点也没现出饿相与萎顿的模样。相反,他却越讲越起劲,越讲越兴奋,鼻子通红通红,脸上的皱折变稀变浅。
讲到棉花,老汉突然大笑起来。他说:“棉花好哇!棉花好哇!那年你爷爷说,豁上饿几个月肚子,也得种它半亩棉花!那年咱家的棉花长得真好呀,一棵上结十几个桃!到秋天,收了十三斤二两!这棉花干啥的?给我娶亲用的!给我套了新棉袄新棉裤,给你娘套了新棉袄新棉裤,另外还套了一床大被!那床大被真好哟,真好哟,真好哟,真好哟……”
老汉说到这里,那声音渐渐小下去,那份灿烂的笑容也凝固在了脸上。封二老婆见状,“嗷”地一声坐到地上大嚎。大脚与绣绣同时扑到床边哭了起来。
一个满天红霞的傍晚,郭龟腰赶着他那驮了四麻袋盐的大骡子回到了天牛庙。不过,这一次回来那骡子屁股后头不光郭龟腰一个,还有一老一少两个女人。两个女人一人挎了一个本地少见的洋花布包袱,绣花鞋和下半截裤管上尘土积了老厚。在进围门的时候郭龟腰说是他的姨和他的表妹,守门的两个青旗会员便没多加盘问。只是在两个女人进门的那一刻,二人都同时感到了两个女人瞅他们的眼神以及年轻女人的胸脯极不寻常。
当天晚上,郭龟腰把村长宁可金叫到了自己家中,说他这一回从青口捎回了几样海鲜,让他去喝两盅。宁可金去了,当他在郭龟腰那果然摆着海螺、乌贼、八带鱼等几样菜肴的桌边落座之后,却有一个面皮白嫩胸脯鼓鼓的年轻女人坐在了他的旁边。郭龟腰说是他的表妹,宁可金心想郭龟腰的表妹怎么不像良家妇女呀,但他却被女人身上出的一股力量所诱惑便没做深究。三人便喝。那女人美目顾盼巧舌如簧很快让宁可金有七八分沉醉。这个时候,女人却莞尔一笑去了郭龟腰家的小西屋。看着村长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郭龟腰才说出了女人的真实身份:那是青口的一个窑姐,名号为“活动画”,老女人则是她的养母。最近青口有两个地痞为他争风吃醋,眼看要酿成大祸,母女俩便想到这里躲几天。说完这些,郭龟腰挤挤眼笑道:大少爷,这女人比别人多了东西,你不见识见识?宁可金问是什么,郭龟腰说多了奶子,人人是两个,她却是四个。宁可金一说瞪大了两眼:真的?那我得好好瞅瞅!说着就起身奔向了小西屋。
宁可金这一瞅,直瞅到第二天早晨。待他带着两个青眼眶子走出来,郭龟腰问:“少爷,怎么样?”宁可金笑笑:“是不错。不过叫你狗日的先瞅过了就不好了。”说着紧紧腰带,晃晃悠悠走出门去。
宁可金照常做他村长应做的事情去了,可是郭龟腰却把“活动画”来到村里的消息暗暗传播了出去。于是,陆续有些男人揣上钱到郭龟腰的家里来了。郭龟腰端茶递烟热情接待,“活动画”的老娘则坐在那里一五一十地收钱,有条不紊地安排他们去小西屋的次序。也不知怎么搞的,对这种活动,郭龟腰那患有哮喘病的老婆竟没有任何反对的表示。她坐在墙角,一边艰难地喘息着一边为男人纳鞋底,只在西屋的门响了才停下针锥向外看一眼。小西屋的门轴年久缺油响得很,每有一个办完事出来堂屋里都听得见。每出来一个,挨号者便急急走出去腆着脸问:“嗳,真是四个?”过来人点点头道:“不假,是四个。”于是未遂者便回到堂屋里等,等得坐立不宁。
两三天过去,这件事终于让宁学祥也知道了。他知道这事是在一天早晨。那天他让几个觅汉在牲口棚里出粪,他在外头正坐着抽烟,忽听里面的老熊笑嘻嘻地问小说:“哎,让你舔掉,你尝着味道怎样?”小说气急败坏地道:“你还说这事!不叫你说了你还说!”老熊笑道:“到底还是年轻,压不住宝。多玩几回就行了。”停了片刻小说又问老熊:“你说她怎么长了四个奶子呢?”老熊说:“是个母畜牲呗,要不她还干那行?”
宁学祥听他们说得蹊跷,吃过早饭便把老熊唤到自己屋里问。老熊没瞒他,把事情都讲了。原来,昨天他听说郭龟腰家里来了卖身女人,便领着小说一块去了。他本来是不想领小说去的,可是这小子说长到二十多了还没尝过女人啥滋味,非要跟着他不可。到了那里,每人交上一块钱,老熊便让小说先去。可是这小子临阵胆怯,要老熊跟他一起进去,老熊便答应了他。到了那间小西屋里,“活动画”正光着身子,一声不吭躺在灯下。老熊先看了看女人的胸脯子,果见她一对大奶子之下,还长着两个蒜头似的小奶子。这时,他对小说做了个上的手势,小说便浑身哆嗦着脱掉了裤衩子。不料他刚趴下,便一下子跑了马,把人家肚子上弄了一大片。“活动画”一见恼了,非要小说把她肚皮舔干净不可。小说起初红着脸不干,可“活动画”不依,小说只好哭着跪下伸出了舌头。老熊实在看不下去,便为他说情,“活动画”这才放过了他……
宁学祥听了这件事后一颗老心忍不住阵阵骚动。自从老婆过世以后,曾有人劝他续弦,但他始终没放在心上。他想自己这一把年纪了,还弄那事干啥?与其再花钱续弦,还不如再多置二亩地呢。再说他想要女人还是有的,李嬷嬷就是现成的一个。李嬷嬷三十一岁上来这里当了老妈子,至今已是十四年了。十四年里,偷偷摸摸跟他睡了也有几十回。宁学祥很仗义,每睡李嬷嬷一回都私下里给她一块面值二十五文的铜板。老婆死后,宁学祥每逢夜里睡不着觉便让李嬷嬷到他的屋里来,每次也都将一个铜板如数付给。他曾不止一次地在与李嬷嬷睡完后想:有这么个又方便又便宜的老尿壶,还费力劳神地续弦干啥呀!
然而今天听说了“活动画”,宁学祥突然想起了李嬷嬷那一身多皱的老皮和她那日渐干涸让他难以进入的穴道。这么一想,便对自己往日的行径感到不满,对年轻女人的身体充满了渴望。他思想了一天,终于在傍晚时把老熊扯到自己屋里,给他两个铜板,让他今夜将“活动画”领来送到他的屋里。老熊笑笑便答应了。
晚上二更天,老熊果然将女人送来了。那女人坐到床边说:“你是村长的爹?”宁学祥说:“是呵!是呵!”便急躁躁去剥女人的衣裳。把女人的剥完,终于看见了人们传说的奇怪奶子。他伸手去揉搓几下,便又大喘着去剥自己的衣裳。待将一个老身子暴露在灯下,女人突然抓住他的腹下之物嘻嘻笑道:“哎哟,跟你儿长得一个样儿!”
宁学祥觉得像一盆冰水猛地泼来,那根老筋一下子萎得不见了。日他奶奶的,爷儿俩睡一个女人,这算啥事儿!他蹬上裤子去觅汉屋里叫出老熊,让她赶紧把“活动画”送走。
第二天一早,宁学祥把儿子喊起来了好一通火,问他村长是怎么当的,郭龟腰把窑子里的臭女人领到村里伤风败俗他也不管。宁可金见老子提这事自己心虚,便说好好好,我去问问,如果真有这事立马撵人!
当天,有几个青旗会员到郭龟腰家里传达了村长的指令。郭龟腰冷冷一笑:走就走。第二天五更时分,他就牵了骡子,领两个女人走出了天牛庙的围门。
女人走了,宁学祥却一连几天眼前老是晃动着“活动画”那白白嫩嫩的身体。他心里说,女人还是年幼的好呀!还是年幼的好呀!有了这种观点,李嬷嬷便在他眼里成了糟糠烂菜、猪屎狗粪,对她连一点点欲望也没有了。因为好多天得不到召唤,李嬷嬷甚为惊奇,这一夜主动去了宁学祥的寝室,却遭到主人一顿臭骂,说她老不要脸,只剩下一把皮了还骚不够。老女人让他骂得羞愧万分,以后再不敢造次了。
又过了十来天,因为一个人的登门,宁学祥老爷多日的朦胧盼想突然有了一个具体的目标。
那人是费大肚子。他带着明显的一脸菜色走进这个大院,结结巴巴地向宁学祥讲,他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让宁学祥开开恩借几升糁子给他。如电光石火闪过一般,宁学祥脑子里倏地形成一个念头。他便瞅着这个失业已久的老觅汉说:“几升糁子能吃几天?要弄就多弄一点。”费大肚子想不到眼前的人开口竟开得这么大,遂感激涕零:“老爷你要能多给最好了。不过也不能太多,太多了我还不起。”宁学祥说:“那就先弄一百斤吧。”费大肚子说:“弄一秤?怕是太多了。”宁学祥道:“你家五六口人,一秤还算多?快弄去就是!”
就在费大肚子兴高采烈地与老婆孩子吃了三天糁子煎饼之后,花二媒婆扭着一双小脚走进了他的家门。费大肚子问她来干啥,花二媒婆说:“给你家办好事呗!”接着,这女人就讲,她今天来是受宁学祥老爷的托付,想让银子给他作填房去。费大肚子一听立即骂起来:“这个老杂种也想得太离谱了,我闺女才多么大?”费大肚子的老婆也说不行,年纪差得太多了。花二媒婆这时微微一笑:“你们不是缺粮食吗?老爷说了,吃完这一百斤,还可以再去弄。另外,你不是想种他家的地吗?你想揽多少他就给多少。”费大肚子两口子还是不答应,说再怎么着俺也不能糟蹋了闺女。
然而,此时一直没有说话的银子开口了:“爹,娘,二婶子说的也是好事,我去吧。”她的爹娘没想到闺女会这么说,都转过脸瞪着眼瞅她。闺女又说:“叫俺去吧,总比一家人饿死强。”于是,两口子便一起落泪了。
以后的几天里,花二媒婆在宁家大院与费大肚子家之间走了几个来回,便把事情定妥了:宁学祥再给费大肚子三秤糁子,等秋后拨十亩地给他种。半个月后也就是七月二十,银子进宁家的门。
这门亲事很快传遍了全村。自然有许多人背地里骂宁学祥老不着调,仗着有钱就干那伤天理的事;也有人骂费大肚子,说他实在没有本事养家糊口了,竟然走了卖闺女这条道。但骂归骂,一些佃户仍是想到了应该给宁家送喜礼——怎能不送呢?眼看就要收秋了,如果不送礼人家收完秋要抽地咋办?
这样,宁家大院又是人来人往。
封铁头也知道了这件事情。他没种宁家的地用不着送礼,然而这件事情却让他痛苦得如万箭穿心。他再怎样也没想到,让他暗恋多年的银子竟要嫁给宁学祥了!想一想银子的美好,再想想宁学祥那老东西的龌龊,他忍不住生出一份要杀人的念头!可是,看看自己多病的老娘,想想仍在人家当着的儿子,他又咬牙强逼着自己打消那个念头。晚上,他躺在床上一遍遍在心里念叨:银子!银子!念叨一会儿,便骑到傻挑身上疯。傻挑让他弄得挺受用,便嘿嘿大笑。这笑把铁头笑醒了,提起巴掌便去猛扇她。傻挑便又哭着哀号:“俺不敢啦!俺不敢啦!”铁头满腔愤懑地收起巴掌,这时泪水早已流了满腮。
七月二十很快到了。这天一大早,一顶绣花小轿便由七八个吹鼓手跟着,从宁家大院出,走过三条街到费大肚子家将新媳妇接走,吹吹打打原路返回。天牛庙的多数村民,又呼呼隆隆涌上街头看了一次热闹。
看热闹的人群里没有铁头。他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走出村子去了远远的山沟里。他到一棵老合欢树下,铺下带来的破蓑衣躺了上去。这儿,除了鸟儿的鸣声别的声响一点也没有,但铁头还是听见了那些吹吹打打。而且,这声音是那么响亮,那么持久,从天明响到了日出,从日出响到了日落!
天黑下好久了,铁头才爬起身,一步一步慢慢走回了村子。走到宁家大院,他贴着墙根,在夜幕的掩护下悄悄摸到了院子的后墙下。他知道墙那边就是宁学祥住的屋子。抬头看看,一个算盘大、贴红纸的小扁窗高高地亮着,在这无边的黑暗里恰似一摊鲜血。铁头蹲在那里,艰难地屏住呼吸去听屋里的动静。
他听见了。他听见老杂种在催促银子上床。他没听见银子说话,但他听见了床铺的细微声响。过了片刻,那小窗户突然没有了灯影。在这如铁一般沉重的黑暗中,铁头觉得自己的心一下子蹦出胸腔,与自己的脑袋合而为一且一下下地涨,直涨得大如油篓!这时候,银子的一声惨叫隔墙传来,铁头那个大如油篓的脑袋突然“轰”地一声爆炸了!在那团爆炸的火球中,有一个老辈人讲过的恶毒戏法流星般飞旋而出。他“嗖”从地上蹿起,高高抡起两只手掌向面前的墙上猛力一拍,同时大声喝道:“锁!”
这么做过,铁头没在这里停留。他弯下腰,趁着黑暗,像条狗一样急急溜走了。
铁头这个做法的后果到第二天早晨才被人现。哭了一夜的李嬷嬷擦干眼泪,硬起心肠为新郎新娘做好早饭,却怎么也敲不开那扇门了。她敲不开门心里越痛苦,忍不住又将眼泪往褂襟上洒。她只好再回到厨房里等。但等到日上三竿,新房那儿却传出宁学祥的呼救声。李嬷嬷走到窗外往里看,看见了一个让她肝肠寸断的场面:那位宁老爷还光着身子与年轻的新娘迭在一起。李嬷嬷大着胆子道:“你没个够就没个够,喳呼个啥?”宁学祥却哭唧唧说:“你快给想想办法,我跟她分不开了……”
李嬷嬷这才明白他的东家遇到了什么事情。这种在新婚之夜生的十分罕见并让新郎新娘难堪万分的怪事,她早就听说过,但她没想到她的东家也会这样。报应!报应!李嬷嬷心里充满了快感。
不过,她并没忘了自己的奴仆身份和一个奴仆应尽的职责。于是,她急忙扭过身,颠儿颠儿地去找对男女之事十分精通的花二媒婆去了。
花二媒婆闻讯后捂鼻忍笑赶来,略施小技就解救出了这一对男女。银子穿上衣裳,趴在床上哭个不止;宁学祥则哭丧着老脸让李嬷嬷和花二媒婆别把这事说出去。两个老女人唯唯喏喏,但就在当天全村便有三分之二的成年人知道了这件事情。许多人见了面突然会喊:“锁!”然后会心地大笑。这一笑,就把寻常日子里无数的痛苦与烦恼笑掉了许许多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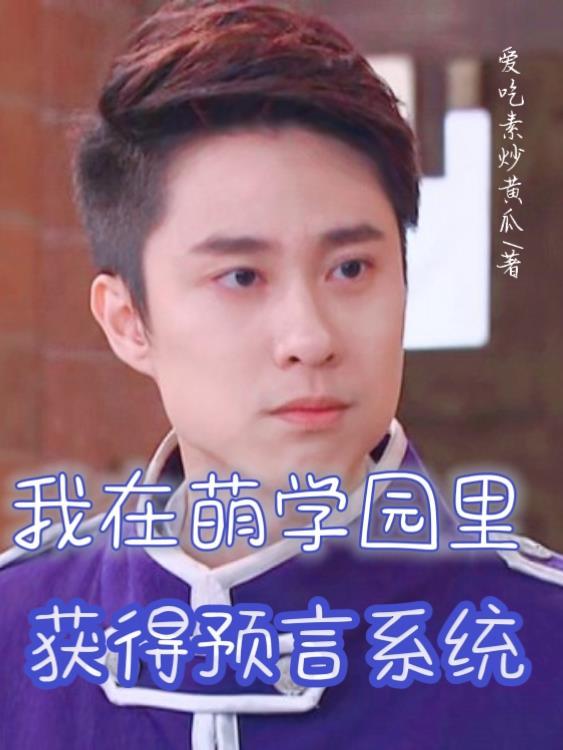
![觉醒女配搞事业日常[八零]+番外](/img/360918.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