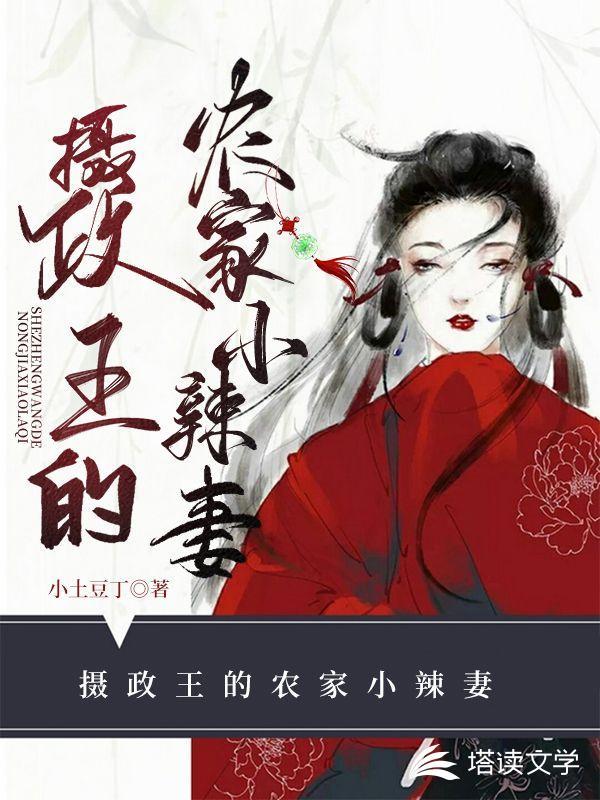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明风再起 > 第330章 山海关大战(第9页)
第330章 山海关大战(第9页)
李过清点残兵时铁甲哗啦作响,左光先的几千人正在往永平城头搬运火器。谷可成接过令箭的手微微颤抖,这一万断后部队要面对的是多尔衮的八旗铁骑。
北京城四月的风,本该带着点暖意,卷起御道两侧新抽芽的柳絮。可崇祯十七年的这个四月,风里裹挟的,只有浓得化不开的血腥、烟灰的焦糊,还有一股子从皇城根儿、从无数朱门大户里渗出来的、绝望的霉烂气儿。紫禁城,这座曾经象征着无上威严的庞然大物,如今像个被掏空了五脏六腑的巨兽骨架,空荡荡地戳在灰蒙蒙的天底下,死气沉沉。只有午门外,那些被大顺军兵士匆忙用清水冲刷过、却依旧顽固地洇着大片大片深褐色印记的巨大青石板,无声地诉说着月余前那场天翻地覆的惨烈。
武英殿,这座在崇祯朝后期被冷落的偏殿,此刻却成了整个大顺王朝短暂国祚的心脏——如果这颗心还能跳动的话。殿内弥漫着一股古怪的混合气味:新刷的劣质金漆刺鼻的味道,劣质香烛燃烧的呛人烟雾,角落里堆积的、尚未完全清理干净的陈年灰尘气,以及一丝若有若无、仿佛从殿宇深处木头缝隙里渗出来的、前朝留下的腐朽气息。
牛金星一身簇新的大红蟒袍,头上的乌纱帽翅随着他急促的步伐微微颤动。他站在空旷大殿的中央,背对着那张临时搬来、铺着明黄色绣龙锦缎的宽大龙椅,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他手里捏着一份薄薄的、墨迹似乎还未干透的礼单,手指因为用力而关节白。几个穿着同样不合身新朝官袍的礼部官员(原明朝降官)垂手肃立在下,大气不敢出,额角都沁着细密的汗珠。
“牛丞相,”一个须花白的老礼官声音颤,腰弯得更低了,“实在是…实在是仓促啊!冕旒冠上的玉珠只凑齐了九旒,按古制天子当用十二旒…衮服上十二章纹,也只绣了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六章…郊祀用的牺牲,最好的也只有一头太牢,少牢都凑不齐整,只能用羊羔充数…祭天的玉帛…更是…”
“够了!”牛金星猛地转过身,脸上惯常的儒雅温和早已被焦灼和一种强压的戾气取代,眼神锐利得像刀子,刮过那几个瑟瑟抖的官员,“都什么时候了?还跟本相扯什么古制章纹!闯王…不,陛下明日就要告祭天地,登临大宝!这是定鼎天下、昭告万民的头等大事!没有?没有就给本相去变!去抢!去借!拆了前朝太庙的旧物也要给本相凑齐了样子!十二旒没有,九旒也成!十二章纹不全,有龙就行!牺牲?一头牛也是牛!玉帛没有,就用上好的黄绫顶上!告诉下面的人,明日大典若出了半分纰漏,本相认得你们,本相腰间的尚方宝剑,可认不得你们项上人头!”
他的声音在空旷的大殿里激起嗡嗡的回响,带着一种歇斯底里的疯狂。几个老礼官吓得面无人色,噗通跪倒在地,磕头如捣蒜:“丞相息怒!下官…下官等这就去办!这就去办!”
牛金星胸膛剧烈起伏了几下,强行压下翻腾的怒火。他疲惫地挥了挥手,像驱赶苍蝇:“滚!都给本相滚出去!日落之前,一切必须备妥!”看着那几个连滚爬爬退出去的背影,牛金星转过身,目光再次投向那张孤零零的龙椅。殿内巨大的蟠龙金柱投下浓重的阴影,将他笼罩其中。他伸出手,指尖在冰凉的龙椅扶手上划过那粗糙的、新镶嵌上去的金龙纹饰,一丝不易察觉的复杂神色在他眼底掠过。是权势巅峰的眩晕?还是大厦将倾前的惶恐?或许连他自己也说不清。他只知道,这出戏,必须唱下去,而且要唱得足够快!
翌日黎明,天色依旧阴沉得如同浸透了墨汁。正阳门外临时搭建的祭坛,在昏暗的天光下显得简陋而仓促。坛高三层,土垒的台基边缘甚至能看到新翻的黄土茬口。坛上摆放着那头作为“太牢”的黄牛,牛角上象征性地系着褪色的红绸,不安地甩着尾巴。旁边是几只瘦小的羊羔,眼神惊恐。供桌上铺着明黄色的绸布,上面摆放的祭品——几盘干瘪的果品,几碟看不出原色的糕点,几碗浑浊的酒水——透着一股难以掩饰的寒酸。那卷替代玉帛的黄绫,皱巴巴地堆在供桌一角。
李自成来了。他没有乘坐那象征着无上威仪的玉辇,只是骑着他那匹伴随他征战多年的乌驳马,在一队盔甲沾满风尘、眼神疲惫的亲兵护卫下,缓缓行至坛下。他身上穿着那件赶工出来的明黄色龙袍,袍服上绣的金龙针脚粗疏,在昏暗光线下显得有些黯淡。头上那顶九旒冕冠,玉珠碰撞出细碎声响,却压不住他眉宇间那深重的、化不开的阴郁。他抬头看了看这简陋的祭坛,又看了看坛下稀稀拉拉、面色惶然、强打精神列队站着的文武官员(大多是原明朝降官和少数大顺老营将领),嘴角似乎向下撇了撇,露出一丝难以言喻的嘲讽,又或者,是浓重的疲惫。他没有说话,只是翻身下马,动作甚至带着点僵硬。
牛金星早已在坛下恭候,见李自成下马,立刻趋步上前,深深一揖,声音带着刻意拔高的激昂:“臣牛金星,恭请陛下告祭皇天厚土,登基称帝,承天景命,抚有四海!”
他的声音在空旷的坛前显得格外突兀,激起几声稀稀拉拉的、有气无力的附和:“恭请陛下登基!万岁,万岁,万万岁!”
李自成面无表情,在牛金星和几个礼官的引导下,一步步踏上那粗糙的土阶。脚步沉重。坛上的风似乎更大了些,吹得他龙袍的下摆猎猎作响,也吹得那九旒冕冠上的玉珠乱晃,在他眼前投下晃动的阴影。他按照牛金星事先反复叮嘱的礼仪,机械地焚香、奠酒、诵读那篇由牛金星捉刀、辞藻华丽空洞的祭天文告。他的声音低沉、沙哑,毫无帝王应有的威仪与激情,倒像是在完成一件极其不情愿的苦役。当读到“臣自成…谨以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时,他甚至微微顿了一下,眼神飘向西北方向,那是山海关的方向,也是他十万精锐折戟沉沙、仓皇败退的方向。一丝难以言喻的痛苦在他脸上一闪而逝,快得让人以为是错觉。
祭天仪式在一种近乎诡异的气氛中草草结束。紧接着,队伍又匆匆返回紫禁城,在同样气氛压抑的武英殿,完成了所谓的“登基大典”。李自成被簇拥着坐上那张宽大的龙椅,接受群臣的“山呼万岁”。那声浪依旧稀薄,透着心虚。龙椅很硬,硌得他很不舒服。他坐在那里,感觉不到丝毫的君临天下,只有一种巨大的、冰冷的空虚和荒谬感,像潮水般将他淹没。他甚至没有仔细看一眼殿下跪拜的人群,目光只是空洞地投向殿门外那片灰蒙蒙的天空。
仪式甫一结束,甚至没等“新皇”说一句场面话,牛金星便猛地从文官班列中跨步而出,再次深深叩,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急迫,响彻整个大殿:
“启奏陛下!军情如火,瞬息万变!山海关之败,虽伤我元气,然天佑大顺,根基犹在!为今之计,当效汉高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智!臣斗胆恳请陛下下圣谕:命满朝文武,所有在京将士,三日内务必整装完毕,护驾西巡!目标——山西固关!凭此雄关天险,重整旗鼓,以图再举!此乃关乎国运存续之要策,万望陛下圣裁!迟则生变矣!”
“西巡”二字,如同冰水泼进了滚油锅!大殿内死寂了一瞬,随即爆出压抑不住的骚动和惊惶的低语!那些刚刚还在山呼万岁的官员们,脸上强装的镇定瞬间崩塌,代之以无边的恐惧和难以置信!三天?只有三天?要离开这座刚刚到手的煌煌帝都?
李自成坐在龙椅上,身体几不可察地晃了一下。牛金星的话像鞭子一样抽在他心上。他缓缓抬起眼皮,目光扫过殿下那一张张惊惶失措的脸,最后落在牛金星那张写满急迫、甚至带着一丝疯狂的脸上。那张脸,在摇曳的烛火和蟠龙柱巨大的阴影下,显得有些扭曲。他沉默着,殿内死寂得可怕,只有粗重的呼吸声此起彼伏。过了仿佛一个世纪那么长,他终于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声音干涩得如同砂纸摩擦,却带着一种冰冷的、不容置疑的决断:
“准奏。”
这两个字,如同打开了地狱的闸门。
“圣谕下——!文武百官!三军将士!三日内撤出京师!护驾西巡山西固关!违令者——斩!”尖利刺耳的传令声,伴随着急促的金锣鸣响,如同瘟疫般瞬间席卷了刚刚经历过“登极大典”的北京城。
整个京城,彻底炸了锅。
那些刚刚穿上簇新官袍、还没来得及享受几天“从龙之功”富贵的大顺新贵们,瞬间慌了手脚。府邸内一片鸡飞狗跳。华丽的衣箱被粗暴地打开,里面的绫罗绸缎、金银细软被胡乱地塞进箱笼、包袱。价值千金的古玩字画被随意丢弃在地上,被慌乱奔跑的仆役踩得粉碎。有人忙着撬开地砖,取出窖藏的金锭银锭,塞进贴身的褡裢,沉重的金属压得他们步履蹒跚。更有甚者,红着眼睛,指挥着家丁冲向还没来得及完全搬空的明朝勋贵府邸,进行着最后的、疯狂的洗劫,只为多捞一点逃亡路上的本钱。哭喊声、咒骂声、争夺财物的厮打声,在朱门高墙内此起彼伏。恐惧和贪婪,将人性的丑恶撕扯得淋漓尽致。
军营里更是乱成一锅沸粥。命令来得太急,各级将佐自己都心神不宁,哪里还顾得上约束部下?那些刚刚经历了山海关惨败、惊魂未定的大顺老兵油子们,早已嗅到了末日的气息。他们丢盔弃甲,成群结队地冲出营房,像一股股失控的浊流,涌向街市。最后的疯狂开始了!商铺被砸开,货架被掀翻,布匹、粮食、盐巴、甚至锅碗瓢盆,被他们哄抢一空。稍有反抗的商贾,立刻被乱刀砍倒。民居也未能幸免,稍有值钱的东西都被搜刮带走。女人的哭喊声,孩子的尖叫声,绝望的哀求声,伴随着兵痞们野兽般的狂笑和呵斥,交织成一末日城市的悲怆交响曲。火光开始在城中的某些角落腾起,那是乱兵在劫掠后放火泄愤,或是焚烧带不走的辎重文书,浓烟滚滚,将本就阴沉的天空染得更黑。
权将军刘宗敏的府邸,此刻成了混乱漩涡中的一个暴风眼。府门前,几辆沉重的骡车已经装得满满当当,粗麻布下鼓鼓囊囊,隐约露出箱笼的棱角和丝绸锦缎的华光。刘宗敏本人却不在指挥装车,他像一头暴躁的困兽,在满地狼藉的前院里踱步,脸上横肉虬结,眼珠子通红。一个管家模样的人连滚爬爬地冲到他面前,带着哭腔:“将军!将军!不好了!东城粮仓那边…看守的几个弟兄…他们…他们自己先抢起来了!还放火烧仓!火势太大,根本…根本救不了啊!那里面…那里面可还有上万石粮食啊!”
“废物!一群废物!”刘宗敏勃然大怒,一脚将那管家踹翻在地,咆哮声震得房梁上的灰尘簌簌落下,“粮食!粮食都没了,老子拿什么养兵?!拿什么去固关?!”他猛地抽出腰间的佩刀,寒光闪闪,“来人!跟老子去东城!看是哪个王八羔子敢动老子的粮!老子活剐了他!”
然而,他刚冲到府门口,一个浑身浴血、头盔都跑丢了的亲兵小校跌跌撞撞地冲了进来,扑倒在地,嘶声喊道:“将军!将军息怒!大事不好!南城…南城朝阳门那边…哗变了!是…是王杂毛手下的老营兵!他们抢了西门守军的骡马辎重,还杀了西门守备,打开城门…带着抢来的东西…跑…跑了!说是…说是要回陕西老家去!挡都挡不住啊!”
“王杂毛?!”刘宗敏如遭雷击,握着刀柄的手青筋暴起,指节捏得白。王杂毛是他麾下一个颇能打仗的老营哨总,山海关败退时还曾拼死护过他!连这样的老兄弟都…都带人跑了?一股冰冷的绝望,瞬间攫住了这位以凶悍着称的权将军。他举着刀,僵立在门口,看着门外街道上更加汹涌混乱、互相践踏奔逃的人流,听着远处越来越近的喊杀声和哭嚎声,只觉得一股腥甜涌上喉头。他猛地回身,不再看那报信的小校,也不再提去东城粮仓,只是对着院子里同样惊慌失措的亲兵们出野兽般的嘶吼:“还愣着干什么?!装车!快给老子装车!能带走的都带上!一个时辰!不,半个时辰后,给老子护着夫人少爷,从西直门走!快——!”
混乱如同瘟疫,疯狂蔓延。曾经象征着大顺权力顶点的皇宫,此刻也陷入了最后的无序。一些胆大包天的大顺兵丁,趁着守卫松懈,翻墙越脊,闯入一座座空寂的宫殿。鎏金的铜鹤、景泰蓝的花瓶、甚至皇帝龙床上镶嵌的玉石,都被他们用刀撬、用锤砸,塞进肮脏的包袱皮。御花园里珍贵的花木被践踏,太湖石上刻下粗鄙的涂鸦。有兵丁为了争夺一个疑似金制的香炉,在空旷的大殿里拔刀相向,血溅龙柱。
而在皇宫最深处,靠近西苑的一处偏僻宫室内,李自成独自一人,站在窗前。他身上那件在祭天和登基时穿过的、针脚粗疏的明黄龙袍已经脱下,随意地搭在旁边的椅子上。他换上了一身半旧的青色箭衣,外面罩着一件磨损得露出内衬棉絮的棉甲,仿佛又变回了那个纵横黄土高原的闯将。窗外,是皇宫层层叠叠、此刻却显得无比压抑的琉璃瓦顶,更远处,是城中冲天而起的火光和滚滚浓烟,还有那隐隐传来的、令人心悸的混乱喧嚣。
牛金星悄无声息地走了进来,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焦灼,但语气依旧保持着恭敬:“陛下,车驾已在西华门外备妥。宫眷和紧要文书也已安排上车。刘宗敏、田见秀等几位将军正在弹压乱兵,清理道路,请陛下移驾!迟恐生变!”
牛金星侍立在不远处,大红蟒袍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格外刺眼。他手里捏着一份誊写得工工整整、墨迹却犹带仓促的撤出人员名册,嘴唇无声地翕动,似乎在反复核对着什么。他眼角的余光却始终没有离开过椅子里那个沉默的身影,额角一层细密的汗珠,在摇曳的烛光下微微亮。殿内死寂,只有李自成那单调的敲击声,和远处隐隐传来的、令人心悸的混乱杂音。
突然!
“报——!八百里加急!永平军报——!”
一声凄厉得变了调的嘶吼,如同淬毒的冰锥,猛地撕裂了殿内凝滞的死寂!一个浑身泥污、几乎看不出本来颜色甲胄的信使,如同从血与火的炼狱中滚爬而出,踉跄着撞开殿门,扑倒在冰冷的地砖上!他头盔歪斜,脸上糊满了汗、血、泥浆的混合物,肩头一支折断的羽箭兀自随着他剧烈的喘息颤抖着。他手中死死攥着一卷被汗水、血水浸透得黑的军报文书,高高举起,那嘶哑的喉咙如同破旧的风箱,拼尽最后一丝力气挤出几个字:
“永…永平…败…谷…谷将军…战殁!左…左帅…坠马…失踪!吴…吴三桂…清虏…追兵…已破抚宁…离…离京师…不足百里了——!”
“轰——!”
这寥寥数语,如同九天惊雷,狠狠劈落在死寂的殿堂!那卷被血污浸透的文书,仿佛有千钧之重,“啪嗒”一声,从信使颤抖的手中滑落,掉在冰冷的金砖地上,溅起几滴暗红的血珠。
李自成没有回头,依旧望着窗外那片燃烧的天空。过了许久,他才缓缓开口,声音低沉沙哑,带着一种刻骨的疲惫和荒凉:“牛丞相,你说…这登基,这祭天…像不像一场梦?一场…刚做就醒了的噩梦?”
牛金星心头猛地一跳,脸上肌肉抽搐了一下,强笑道:“陛下何出此言?此乃承天应命,万民归心!些许小挫,何足挂齿?待到了固关,整军经武,不消一年半载,必能重振旗鼓,再克京师!”
李自成终于转过身,目光落在牛金星那张强作镇定、却难掩仓皇的脸上。他的眼神锐利如昔,仿佛要看穿对方所有的掩饰。牛金星被他看得心头一阵毛,不由自主地避开了视线。
李自成嘴角扯动了一下,似乎想笑,最终却只化作一声几不可闻的叹息。他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弯腰,拾起搭在椅子上的那件明黄龙袍。入手沉重,刺绣的金龙冰凉。他看也没看,随手将那象征着至尊权力的袍服,如同丢弃一件破布般,揉成一团,扔在了冰冷的地砖上。
“走吧。”他吐出两个字,声音平淡无波,径直越过躬身侍立的牛金星,大步向门外走去。脚步踏过那团刺眼的明黄,没有丝毫停留。门外昏暗的光线勾勒出他箭衣棉甲的背影,显得异常单薄而决绝,迅融入门外更深的阴影与远处映天的火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