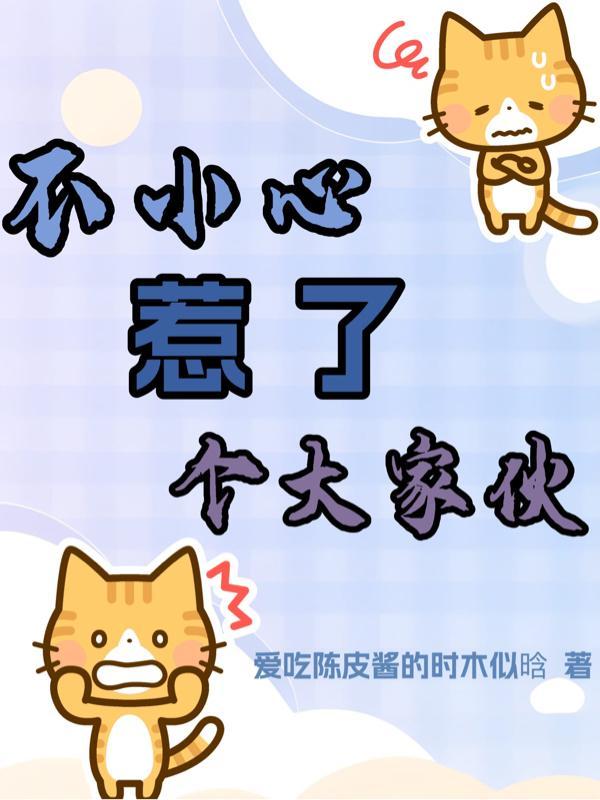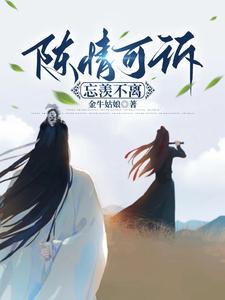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这个藩镇过于凶猛 > 第181章 刺史之智闻所未闻(第2页)
第181章 刺史之智闻所未闻(第2页)
刘靖也不好解释,干脆默不作声,认下了这份功劳。
只能在心中默默给张居正道了声歉。
一条鞭法与摊丁入亩在这个时候出现,完全是划时代的。
须知,唐时以前,赋税是分开的。
赋是赋,税是税。
唐朝德宗时,实行两税法,统一赋税,同时也不必再区分土户、客户等,只要在当地有资产、土地,就算当地人,就需上籍征税。每年两收,分别在夏收与秋收之时征税。
但,两税法只是统一了赋税,却并未统一徭役。
地方兴修水利,便会征民夫,这是一种徭役。
打仗征随军民夫,亦是一种徭役。
类似这样的徭役有许多,一句两句说不清楚。
唐时规定,上至五十六,下至二十三的男丁,每人每年需服役二十日。
如果有人不想去,或因各种原因无法去,那怎么办?
简单,花钱!
若不服役,可每日纳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抵充,称为“庸”??。
而一条鞭法将赋税与徭役,全部统一。
不想服徭役,直接交钱,官府会用这笔钱,去雇佣人顶替你去。
如此一来,使得税收更加简洁精干,也能防止官员佐属趁机上下其手。
摊丁入亩,则是对一条鞭法的补充。
可以理解为,是对上个版本打的一个补丁。
这其中涉及的核心,是对公平的重新定义。
问大伙一个问题,什么是公平?
在摊丁入亩之前,徭役是按人头算,不论贫富,只要是成年男丁,都需服徭役。
这是不是一种公平?
对富人来说,很公平,但对贫苦百姓来说,不公平。
富人有钱,且家中男丁也就那么几个,只需缴纳一些绢布,便能免于徭役,省下的时间继续用于赚钱。可贫苦百姓本来就穷,家中只有几亩薄田,活下去已经很艰难了,每年还需服二十日的徭役。
而这样的公平,自秦始,一直持续了数千年。
直到明朝,张居正站了出来,说这样不对,得换一个公平。
于是,有了一条鞭法。
所谓摊丁入亩,是将人头与田产挂钩,田多者多服役,田少者少服役,无田无产者不服役。
富人田产多,就必须承担大部分徭役,从而多交钱,官府拿这笔钱,再雇佣百姓去服役。
如此一来,徭役有人服了,官府的事办成了,服徭役的穷苦百姓也有钱拿,能够补贴家用,一举三得。
这就变成了,对富人不公平,但对穷苦百姓公平,相当于劫富济贫。
两者都公平,主要看你如何定义。
任何一个当权者,只要不是傻子,都会选择后者。
一旦实行,穷苦百姓的压力将会骤减,肩上的担子轻了,也就能养活更多的孩子,人口暴增,生产力提高,形成人口红利。
而火耗归公,则是又一个补丁,针对基层官员和胥吏,防止他们对百姓上下其手,同样也是为了保证百姓的权益。
然而,正常情况下,摊丁入亩、火耗归公的推行很困难,因为这得罪了权贵、富人以及基层胥吏的利益。
但,刘靖现在推行,却非常简单。
先歙州已经被陶雅血腥屠杀一波,世家大族被屠戮一空,剩下的都是些小地主和商贾,翻不起风浪,即便有心抵抗,可在刘靖的大军面前,也不敢表露。
这年头,拳头大就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