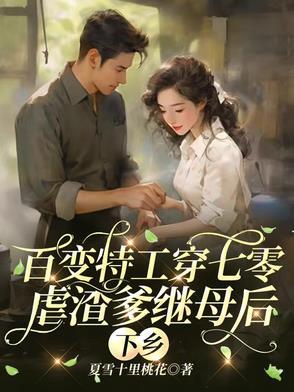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这个藩镇过于凶猛 > 第181章 刺史之智闻所未闻(第1页)
第181章 刺史之智闻所未闻(第1页)
公廨之中。
刘靖拿着一本册子,正在与胡三公商议。
唐时实行三省六部制,同时下放到州,同样也是这套模版。
一州刺史总揽全局,别驾、长史、司马三人从旁辅佐协助,而对应六部的,则是六曹,分别是功、仓、户、兵、法、士六曹参军事,主管税收、诉讼、治安、教育、户籍、司法、工程营造等。
而到了县,就戛然而止。
除了长安、万年等京畿重县设有六曹之外,其余州郡下辖的县,班子只有县令、主簿、县丞,余下就是佐属胥吏。
县之下的乡,则只有一个里长。
里长往往是由村中德高望重的乡贤担任,而南方乡村宗族观念极强,所谓乡贤,常是一村大姓的族长。
很多时候,里长的话比县令都好使,更拥有生杀大权。
尤其是一些坐落在山疙瘩里的村子,长期与世隔绝,里长就是当地的土皇帝。
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
县以上的这套班子,刘靖不打算大改,只是稍稍改动,使得架构更加精简,各部门职务也更加清晰明了,如此可提升办事效率。
这也是刘靖的优势所在,自秦以来,汉、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每个朝代,都在原有的基础上,对上一任政府框架进行优化,这是一代代先贤的集体智慧,而他却能直接拿来用。
就比如科举制,并非一蹴而就,最早源于南北朝时期的萧衍,到了隋朝,慢慢有了雏形,等到了唐初,在李二凤的推动下才正式定型。
但科举制真正普及,并扬光大,是在宋朝。
这其中的跨度,足有五六百年之久,历经了几十代人的共同努力。
县级以上框架暂时不动,但县级以下,他打算动一动。
作为一个后世穿越而来的人,接受过教员思想,让他对基层民众放任不管?
开什么国际顽笑!
基层群众的力量有多大,没人比他更清楚。
况且,不掌控乡村,他接下来的政策也就无法顺利推进。
“乡村设村办,设村长、里长、村书记,异地而任……这会不会显得太过臃肿,导致冗官,且每村设三人,歙州之地乡村零零总总加起来足有二三百,这就是近千人了,俸禄支出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胡三公看着手中改制书,不由皱起眉头。
他已经代入别驾的职务,所思所想,自然也非一县县令那般局限狭隘。
近千人的俸禄,可不是一笔小钱,每月至少上千贯,一年下来就是数万贯。
“这是必要的支出,省不得。”
刘靖说着,又将另一份册子递过去:“三公且在看看这个。”
“好。”
胡三公接过册子,将单照凑到右眼上,仔细查看。
单照,又称叆叇,是唐宋时期的老花镜。
是的,这会儿就已经有老花镜了,只不过还很简陋,只有一片镜片,通常是用质地通透纯净的水晶打磨而成。
胡三公到底是老了,老眼昏花,不借助单照,没法看清那些蝇头小字。
看着看着,他脸色变了,无比凝重。
待看完之后,胡三公放下册子,目光震惊的看着刘靖,久久不语。
对方的反应,刘靖并不意外,问道:“三公觉得如何?”
胡三公感慨道:“好一个摊丁入亩,好一个火耗归公,好一个一条鞭法,老拙一直不信有生而知之之人,而今却是开了眼。刺史之智,老拙闻所未闻。”
这是仁政啊!
可谋万世之基的仁政!
而这样的仁政,却出自一个未及冠的少年之手,这让胡三公如何不震惊。
宦海沉浮几十载,什么样的妖孽他没见过?
但刘靖这样的,还真是头一回儿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