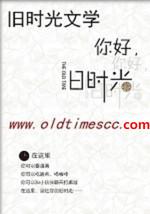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明末封疆 > 第670章 旧物(第1页)
第670章 旧物(第1页)
成都北郊,校场之上,旌旗蔽空,甲胄鲜明。
一场盛大而肃杀的献俘仪式,正在按照古礼进行。
这是魏渊刻意安排的,既是为了彰显朝廷平定四川叛乱的武功,更是为了震慑所有心怀叵测之徒,尤其是那位即将被“邀请”来的特殊观众。
校场中央,筑起了一座高大的献俘台。
台上,魏渊身着御赐的蟒袍玉带,神色肃穆,端坐于主位。
两侧文武官员按品级肃立,新军将士盔明甲亮,持戈环列,森严的气氛令人窒息。
号角长鸣,鼓声雷动。
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一队精锐的士兵押解着一长串垂头丧气、身戴重枷镣铐的俘虏缓缓进入校场。
这些多是孙可望军中的骨干将校,此刻皆如丧考妣。
而队伍的最前方,正是昔日不可一世、如今却形容枯槁、面色惨白的贼酋孙可望!
他被剥去了甲胄,穿着一身肮脏的囚服,沉重的木枷和铁链几乎压弯了他的腰,每一步都踉跄蹒跚,全靠两旁的军士架着拖行。
他的眼神空洞,早已没了往日的气焰,只剩下无尽的恐惧和绝望。
刘文秀全身披挂,大步走到台前,单膝跪地,声音洪亮,带着大仇得报的激愤与忠诚:
“启禀柱国!末将刘文秀,奉令讨逆,幸不辱命!今已擒获贼酋孙可望及其党羽主要头目,献于麾下!请柱国示下!”
魏渊缓缓起身,目光如电,扫过台下黑压压的俘虏和寂静的军队、百姓,声音通过扩音的号角传遍全场:
“逆贼孙可望,悖逆狂狡,僭称名号,荼毒川蜀,罪孽滔天!今赖将士用命,天子洪福,元凶就缚!此乃朝廷之威,法度之严!凡有敢犯上作乱、祸国殃民者,这便是下场!”
“依《大明律》,谋逆大罪,当处以极刑!本柱国宣布:将孙可望,处以剥皮实草之刑!悬示众,以儆效尤!其余胁从,按律严惩!”
“剥皮”二字一出,全场顿时响起一片倒吸冷气之声!
即便是在律法严苛的明代,这也是最残酷的刑罚之一,非十恶不赦之大逆不道者不用此刑!
魏渊此举,无疑是要用最血腥的手段,彻底粉碎所有潜在的叛乱念头。
行刑的过程残酷而缓慢,剥皮公开进行,意在最大化其威慑效果。孙可望凄厉绝望的哀嚎声响彻校场,令人毛骨悚然。
许多官员和百姓都不忍地低下头或移开目光,校场上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和恐惧感。
而就在这令人窒息的氛围中,在高台一侧的特设席位上,一位特殊的观众正襟危坐,面色苍白,额角甚至渗出了细密的冷汗——正是蜀王朱至澍。
他接到魏渊“邀请”时,便知宴无好宴。
隆昌县郭家“投献”土地、借他名号横行乡里之事早已传回成都,他知道魏渊必然要借此难。
但他心中虽忐忑,却尚存一丝侥幸:自己毕竟是太祖皇帝钦封的蜀王,皇室宗亲,地位尊崇然。
魏渊权势再大,说到底也是个臣子,难道还敢对一位亲王如何?最多是训诫一番,罚没些钱财田产罢了。
故而此刻,他虽被那残酷的刑罚所震慑,却仍强自维持着亲王的仪态,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矜持与不满。
漫长的行刑终于结束。校场上的血腥味浓得化不开。
魏渊仿佛刚刚完成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缓缓踱步,来到了蜀王朱至澍的面前。他脸上甚至还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令人难以捉摸的笑意。
“王爷,”
魏渊的声音平静,甚至显得有些随意,仿佛只是在闲聊家常,“今日这献俘仪式,让王爷受惊了。”
朱至澍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干巴巴地道:
“柱国大人为国除害,严肃法纪,本王……本王亦是深感欣慰。”
他实在不想在此地多待一刻。
魏渊仿佛没有听到他的客套,目光看似无意地扫过远处那血腥的行刑台,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用一种近乎闲聊的语气,淡淡地问道:
“哦,对了。说起来,我倒是曾听闻一则轶事,也不知是真是假……据说,王爷府上,好像也珍藏着一张……人皮?”
此言一出,如同平地惊雷!
朱至澍脸上的血色“唰”地一下褪得干干净净,身体猛地一僵,端着茶盏的手剧烈一颤,险些将茶水泼洒出来!他瞳孔骤然收缩,惊疑不定地看向魏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