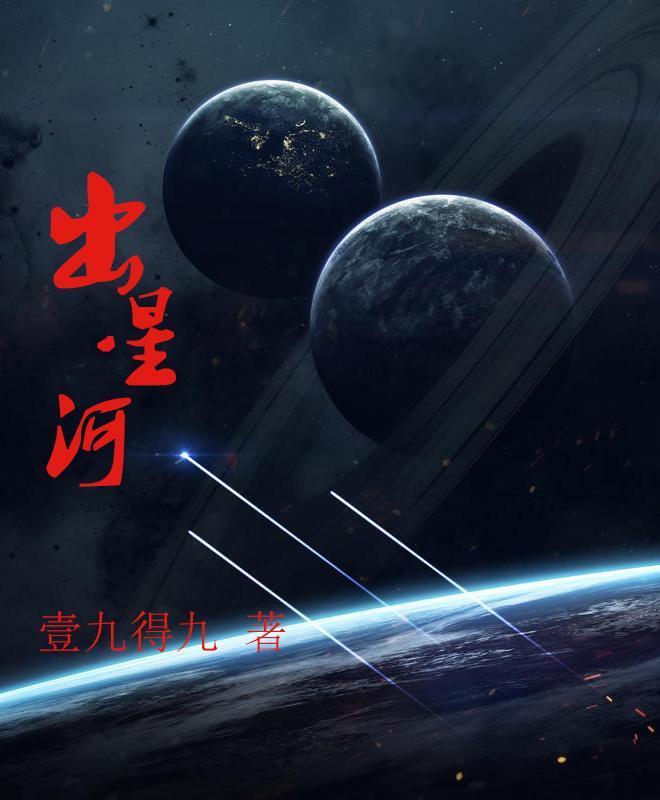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三国:开局长坂坡,赵云是我叔? > 第431章 弟愿誓死追随(第1页)
第431章 弟愿誓死追随(第1页)
獂道城中,太守府。
徐邈身穿武袍,头戴文士冠,有些显得不伦不类。
时值傍晚,晚食之际。
案上无肉,无酒,只有一碟咸菜,一碗菜粥,半张粗饼。
徐邈拾起筷子。
竹筷停在咸菜之上半晌,又在叹息声中落下,重新置于案上。
“兄长三日来寝食难安,只顾叹气,却是何故?”
徐邈闻言,摇了摇头,并不言语。
徐飞见状,抬起鸡腿撕咬一口,又放回木盘中,狠狠咀嚼两口,囫囵吞下。
“大哥,马此番不过是缓兵之计,便是小弟亦能瞧得出来,我等只须据城而守,他纵有数万兵马,如何能进得城来。
也不知大哥为何连日唉声叹气。。。”
徐邈摇头,叹道:
“非是缓兵之计。。。唉。。。”
“大哥,到底为何忧愁,小弟三日来问了数十次,大哥只顾摇头叹息,却一言不,真叫人心焦。”
徐邈闻言,抿着嘴唇,仍旧沉默不语。
“砰!”
徐飞拍案而起,胡乱将手上油脂擦在胸口衣襟,怒声道:
“大哥不说,小弟也知定是马诡计!
大哥勿忧,小弟这便出城迎战,拼死探得马使了甚么阴谋诡计!”
言罢,拱手一礼,便往外疾走。
徐邈见状,急起身言道:
“吾弟且住!”
徐飞停步回头。
徐邈犹豫半晌,叹道:
“唉。。。马之勇,吾弟难道不知?
便是魏王身边的虎侯,亦非其敌手。
武勇之辈,多自恃勇力而不屑用计。
如此熊虎之将,焉能使此攻心之计?”
徐飞道:
“那他为何不攻城,却叫数万大军守在营寨不出?”
徐邈缓缓起身,行至堂前,负手叹曰:
“唉。。。其言,欲书信去成都,劝汉中王罢兵。”
徐飞奇曰:
“若不是计,他说动刘玄德罢兵,不是正合我意?大哥为何烦忧至此?”
徐邈摆了摆手,又负手踱步出堂,站在廊前,仰天看着云卷天边,言道:
“吾弟以为,汉中王刘备,乃何人也?”
徐飞挠了挠络腮胡,答曰:
“往日只听得是当今皇叔,素有仁德之名,不知详细。大哥为何如此问?”
徐邈不答,又问道:
“吾弟以为马乃何人也?”
徐飞闻言,脱口而出道:
“猛将也。。。
唔。。。听闻其父亲宗族皆在许都,因其反叛朝廷而死,其人不孝。”
徐邈微微摇头,不置一评,又问道:
“吾弟以为魏王如何?”
徐飞道:“大哥要作甚?不妨直言,无论如何,小弟唯大哥马是瞻。”
徐邈闻言,轻声道:“汉中王刘备,漂泊半生,屡战屡败,而其志不改,终成今日之汉中王。
向日其所居之地,无论涿郡、洛阳、平原、徐州、乃至新野小县,无人不称其仁德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