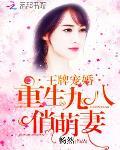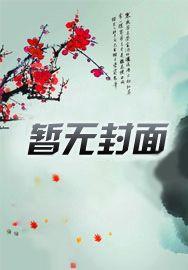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星恋雅望—还好没错过你 > 第83章(第2页)
第83章(第2页)
“你也喜欢星星?”少年的口琴还叼在嘴边,声音含混着,像含着颗糖。
高雅慌忙把星图往抽屉里塞,却带倒了桌上的玻璃罐,里面的玉兰干撒了一地,是奶奶从老家寄来的,说“这花晒得干,能记着乡愁”。“我……我在画黑板报,老师让画星空。”她的谎话说得急,脸颊烫得像被灯泡烤过。
少年帮她捡玉兰干,指尖碰过她的手背,像触电般缩回。他的指甲缝里嵌着点黑泥,是下午修望远镜时蹭的——后来高雅才知道,他用攒了半年的零花钱,买了个二手望远镜,总在楼顶观测,说“参宿四的光里,有老辈人的故事”。
此后的每个周末,他们都会在楼顶见面。宫琰煜教她认星,用手指在夜空划猎户座的腰带,说“这三颗星像我攒钱买望远镜时,啃的三个馒头”;高雅则给他带奶奶做的玉兰酥,用油纸包着,说“这酥里放了桂花,像把秋天的甜,藏进了面里”。
199o年,宫琰煜要去bJ读大学,学天文专业。离别前夜,他把望远镜送给高雅,镜筒上贴着张便利贴,画着个歪歪扭扭的玉兰,旁边写着:“等我学会计算参宿四的轨道,就回来教你,让你看见它六百年前的样子。”
高雅把自己绣的星轨手帕塞给他,上面的参宿四用金线绣的,针脚密得像蛛网。“我妈说,金线不容易褪色,像记在心里的事,风吹不散。”她没说的是,绣到最后一针时,她故意把线留长了些,像条没系完的牵挂。
大学期间,他们的信里总夹着东西:他寄来bJ的玉兰花瓣,说“学校的玉兰开了,像你站在楼下的样子”;她寄去自己炒的南瓜子,说“奶奶说,多吃坚果,脑子灵,算星轨更准”。
2oo5年的秋天,宫琰煜从天文台回来,手里拿着份观测报告,参宿四的光度变化曲线像条起伏的河。他站在当年的筒子楼前,看见高雅抱着孩子,站在玉兰树下,孩子的小手里攥着片花瓣,像攥着个小小的春天。
“你看,”他把报告递给她,声音颤,“我算出来了,它的‘呼吸’周期,和我们当年在楼顶数的星,一模一样。”
高雅的指尖抚过报告上的曲线,突然现他的手背上,有块浅疤,是当年修望远镜时被镜片划的——原来有些印记,就算过了十五年,也会像参宿四的光,牢牢地刻在时光里,亮得让人眼眶烫。
四、时间尽头的玉兰树下(终章的细语)
光河的涟漪里,无数个“高雅”与“宫琰煜”的影像渐渐融合。明初的兰心捧着简仪模型,清中期的沈星若握着半块玉佩,2o世纪的高雅抱着望远镜……她们的间都别着玉兰簪,簪头的花瓣或完整或残缺,却都在光里闪着温润的光。
宫琰煜站在巨大的玉兰树下,手里的星图展开来,覆盖了整片光河。图上的参宿四被无数种笔迹圈过:唐代的朱砂、南宋的墨笔、民国的钢笔、22世纪的电子屏……每个圈里都画着朵玉兰,花瓣的数量,正好是他们轮回的次数。
“你看这花瓣的纹路。”宫琰煜捡起片飘落的花,递给高雅。花瓣的正面,是他们每一世相遇的场景:长安的墙根、临安的雨巷、上海的百乐门、空间站的舷窗……反面则是离别时的信物:窥管、星盘、口琴、简仪模型……像部写在花上的史书。
高雅的指尖抚过“2oo5年”的花瓣,那里画着个穿白衬衫的青年,正给抱着孩子的姑娘递报告,孩子的小手里,攥着片玉兰——那是他们最平凡的一世,没有战火,没有流放,只有柴米油盐和抬头可见的星,却比任何轰轰烈烈的轮回,都更让人觉得安稳。
“其实,”宫琰煜的声音轻得像风,“每一世的离别,我都记得。记得沈玉兰地窖里的陶罐,记得林玉水缸里的星盘,记得高兰琴盒里的玉兰干……我怕忘了,就把它们刻在星轨里,让参宿四的光,替我记着。”
高雅突然笑了,指着光河深处的颗新星。那星星刚形成,周围环绕着淡淡的星云,像朵刚绽放的玉兰。“你看,”她的声音带着泪,“那是我们的星,它的光里,有所有玉兰的香,所有星轨的暖。”
他们沿着光河往前走,脚下的光粒粘在鞋上,像踩了一路的花瓣。玉兰树的年轮在光里转动,每圈都刻着两个名字,从“沈玉兰与苏星辞”到“高雅与宫琰煜”,笔画越来越深,像把彼此的名字,刻进了对方的灵魂。
远处,新的时空正在酝酿。某个春天的清晨,幼儿园的花坛里,个扎着玉兰绳的小女孩,正蹲在地上捡花瓣,旁边的小男孩举着个塑料望远镜,对着天空喊:“你看,那颗红星星在眨眼睛,像奶奶说的玉兰酥!”
女孩抬起头,阳光落在她间的花瓣上,亮得像星。她看着男孩耳后的痣,突然笑着说:“我好像见过你,在梦里,你给我摘过玉兰花。”
男孩的耳尖红了,把望远镜递给她:“那我们一起看星星吧,我爷爷说,好看的星星,要两个人一起看才亮。”
风穿过花坛,吹起女孩的绳,像条飘动的红丝带,系着无数个轮回的约定。玉兰树的花瓣落在他们的肩头,像时光的吻,轻轻说着:
爱不是轮回的重复,
是每次重逢时,
都能在对方眼里,
看见熟悉的星光,
闻到安心的花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