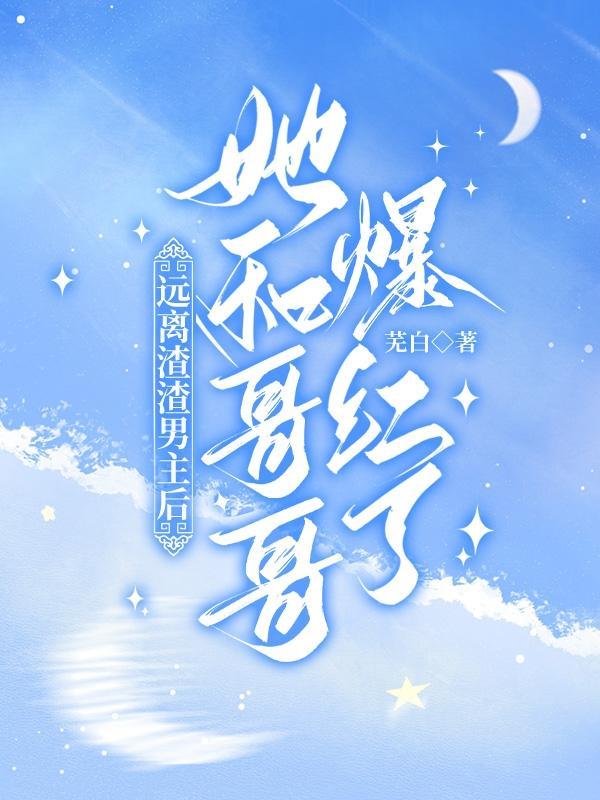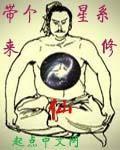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诡异的公交车 > 第263章 褶皱之忆(第1页)
第263章 褶皱之忆(第1页)
我瘫坐在靠窗的位置,身体像被抽走了所有力气,只剩下一具空壳在微微颤抖。意识在崩溃的边缘来回摇晃,仿佛下一秒就要坠入无底深渊。我用力掐住自己的手臂,指甲陷进皮肉,尖锐的痛感从神经末梢直冲大脑——是真的,不是梦。这疼痛如此清晰,如此具体,它像一根铁钉,将我钉在这诡异的现实里。
红裙小女孩的倒影消失了。那个站在车窗玻璃外、湿漉漉的头贴在脸上、眼神空洞的小女孩,刚才明明就站在雨中,隔着玻璃与我对视。可现在,窗外只剩下模糊的雨幕,车窗像蒙了一层雾,什么也看不清。但我清楚地知道,她不是幻觉。她的存在,比这车厢里的冷空气、比雨点敲打车顶的节奏、比座椅散出的陈旧皮革味还要真实。
我强迫自己冷静,试图用理性去解释这一切。心理学课上讲过,人在极度疲惫、恐惧或感官剥夺的状态下,容易产生集体催眠或环境暗示,从而引幻觉。可这里的一切太真实了。我能感觉到膝盖上凉意渗入布料,能听见雨滴砸在车顶的“噼啪”声,甚至能闻到前排乘客身上淡淡的香水味混着潮湿的霉味。这不是幻觉能模拟出的细节。
除非……真实本身,已经被扭曲了。
这个念头像一根冰冷的针,刺进我的脑海。我突然想起大学时在一本冷门心理学期刊上读到过的理论——“时间褶皱”。那篇文章说,在某些极端情绪或强烈集体信念的作用下,空间会像布料一样生折叠,时间不再是线性流动,而是出现循环、错位,甚至局部停滞。就像布匹被揉皱,原本相隔遥远的两点突然贴在一起。那些民间传说中的“鬼打墙”、“鬼压床”、“夜行遇旧人”,或许并不是迷信,而是人类对这种时空异常最原始的描述。
而在这辆1o7路公交车上,某种“褶皱”正在生。
“反应”——这个词在我脑海中反复回响,像钟声一样沉重。从上车开始,它就不断出现在我的感知里:广播里模糊的低语、车窗上浮现的字迹、红裙女孩嘴唇无声开合的口型……都在说同一个词:“反应”。可我还不知道,我该“反应”什么。
我抬起头,看向司机。他始终沉默,背影僵直,制服肩章上的编号模糊不清。我盯着后视镜,想从那小小的镜面中捕捉一点线索。可就在那一瞬,镜中的脸开始融化。
不是夸张的比喻,是真正的融化。他的皮肤像蜡烛受热般软化、滴落,露出下面层层叠叠的面孔——一张男人的脸浮现,随即被一张老妇人的脸覆盖;一个少年的轮廓刚成形,又迅扭曲成中年女人的惨白面容。每一张脸都带着痛苦的表情,眼睛空洞,嘴角下垂,仿佛在无声地呐喊。他们不是死去的乘客,他们是曾经“反应”过的人,被困在这辆车的褶皱里,成了时间的残影。
“你们……都是乘客?”我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几乎听不出是自己的。
司机没有回头,也没有回答。可就在这时,车厢顶部的广播突然“滋啦”一声响,像是老旧磁带被重新播放。接着,一个稚嫩的小女孩声音缓缓响起,带着机械的回音:
“1o7路,终点站:遗忘之桥。请乘客注意,您的‘反应’将决定下车时间。未反应者,永远循环。”
那声音像冰水灌进我的耳朵,顺着脊椎一路流到脚底。我猛地攥紧座椅扶手,指甲几乎要抠进皮革。原来如此——这辆车根本不是交通工具。它是一道筛选机制,一个困在时间褶皱中的审判场。它不载人去目的地,它载人去“觉醒”。
每一个上车的人,都是在某种情绪或记忆的临界点被卷入的。而“反应”,不是简单的害怕或惊叫,而是对真相的认知,对过往的直面,对内心最深处恐惧的承认。只有真正“反应”了的人,才能打破循环,抵达终点。
而我……刚才掐自己手臂时的恐惧,不是“反应”,只是本能。
真正的“反应”,是面对那个我一直逃避的记忆——三年前的那个雨夜,我坐在副驾驶,母亲开着车,1o7路公交从对面冲出来,刹车声刺耳,撞击的巨响,玻璃碎裂的瞬间……而我活了下来,母亲没有。
那天之后,我选择性地遗忘了那段记忆。医生说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自我保护机制。可现在我明白了——那不是遗忘,是逃避。我从未真正“反应”过那场事故带来的痛。
车窗外,雨更大了。一道闪电划过,照亮了路边一座石桥的轮廓——桥身斑驳,桥下没有水,只有一片浓得化不开的黑雾。桥头立着一块锈迹斑斑的路牌:遗忘之桥。
广播再次响起,还是那个小女孩的声音,但这次,语调变了,带着一丝诡异的期待:
“乘客林晚,检测到初步情绪波动。恐惧已记录。请继续反应。否则,下一圈,开始。”
车厢灯光忽明忽暗,我看见其他乘客的身影在座位上渐渐透明,像被时间慢慢抹去。他们的脸没有表情,眼神空洞,仿佛已经循环了千百次,灵魂早已枯竭。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还在颤抖。但这一次,我不再掐它。我闭上眼,任由记忆的潮水涌来。
母亲的手握着方向盘,哼着歌。雨刷器左右摆动。我说“妈,我饿了”,她笑着说“到家就给你煮面”。然后是刺眼的远光灯,是失控的转向,是撞击前她最后回头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我从未敢回想。
现在,我终于“反应”了。
泪水滚落,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痛。真实的、撕心裂肺的痛。我张开嘴,声音沙哑却清晰:
“妈……对不起,我一直不敢记得你。”
话音落下的瞬间,车厢剧烈震动。司机的头缓缓转了过来——那已不是人脸,而是一面镜子,镜中映出的,是我童年时的模样,坐在母亲身边,笑着,无知无觉。
广播最后一次响起,声音轻柔,像摇篮曲:
“乘客林晚,反应确认。终点站到达。请下车。”
车门“嗤”地一声打开,外面不再是雨夜,而是一片朦胧的光。桥的另一端,隐约有个身影站在那里,穿着她最喜欢的蓝色风衣,背对着我,似乎在等。
我知道,那是她。
可就在我伸手要去拉开车门时,余光瞥见角落的座位上,一个红裙小女孩正静静看着我,嘴角微微上扬。
她不是幻觉。
她是下一个“我”。
而1o7路,永远不会真正到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