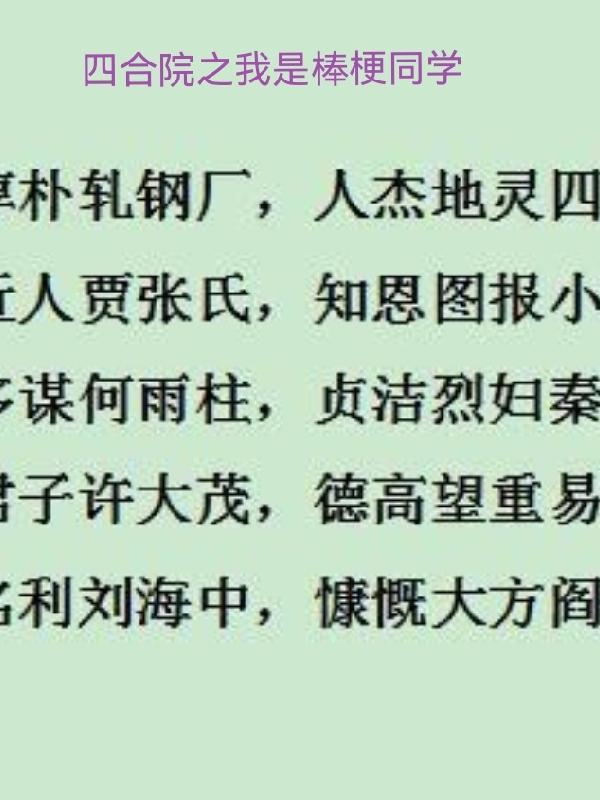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大乾风云起苍穹 > 第249章 县衙报到(第1页)
第249章 县衙报到(第1页)
天刚蒙蒙亮,苏康就醒了。
推开客栈窗户,外面飘着细密的小雨,空气里的酸腐气淡了些,却裹着股湿潮湿的凉意,阴风阵阵。
柳青已经把行李收拾妥当,那些连弩和箭匣都用粗布裹紧,塞进铺盖卷最底层,看着和普通行李没两样;王刚则拎着剩下的竹筒炸雷,藏进马车座位下的暗格里,又去后院牵了枣红马,马料加得足,马儿甩着尾巴,比昨天精神了不少。
“把行李都搬上车,吃完早饭直接去县衙。”
苏康洗漱完,把上任文书揣进怀里,“到了那儿少说话,多盯着周围的动静,别露了兵器的底细。”
三人把行李搬上马车,刚锁好客栈房门,老板就拿着抹布迎上来:“客官这就走?要不要带点早饭?粥是刚熬的,馒头也热乎。”
“三碗粥,六个馒头,就在大堂吃。”
苏康找了张靠窗的桌子坐下,没必要打包,他们吃完后直接坐车去县衙,省得来回折腾。
老板很快把粥和馒头端上来,粥熬得还算浓稠,馒头虽有点硬,却带着麦香。
三人没多话,快吃完,柳青结了账后,三人便坐上马车,离开了悦来客栈。
小雨还没停,打在脸上凉丝丝的。
街上的行人比昨天多了些,大多是挎着竹篮的妇人,篮子里垫着破布,急匆匆往城外走,看那样子,是去挖野菜的。
她们见了苏康的马车,都下意识往路边躲,眼神里满是怯意,连头都不敢抬。
按昨天老头指的路,没走一刻钟就到了县衙门口。
朱漆大门剥落得厉害,露出里面暗沉的木头,门口的两只石狮子缺了耳朵和爪子,看起来破败又滑稽。
台阶上长满了杂草,有的都快没过脚踝,风一吹晃悠悠的,两个穿着褪色皂衣的衙役靠在柱子上打盹,一个脑袋一点一点的,嘴角还挂着口水。
王刚赶着马车停在门口,马蹄踩在青石板上的“嗒嗒”声,终于把两个衙役惊醒。
瘦高个衙役揉着眼睛打哈欠,语气散漫得像在赶乞丐:“干啥的?大清早的,别在这儿挡道,县衙不是你们瞎晃的地方。”
苏康从马车上下来,掏出怀里的文书递过去,声音不高却透着威严:“新任武陵县令苏康,前来赴任。”
这话一出口,两个衙役瞬间僵住了。
矮胖衙役立马站直身子,手忙脚乱地掸了掸衣服上的灰尘,脸上挤出讨好的笑;瘦高个捧着文书,凑到眼前看了又看,又抬头反复打量苏康。
待见到苏康穿着长衫却气度不凡,冷汗一下子就下来了,连忙躬身道:“原……原来是苏大人!小的有眼不识泰山,您稍等,小的这就去请周县丞出来!”
说完,他撒腿就往里面跑,脚步又快又急,哪还有刚才的拖沓劲儿。
矮胖衙役则连忙搬来旁边的石凳,用袖子擦了又擦:“苏大人,您快坐,别淋着雨。小的再去给您沏壶热茶?”
“不必了,就在这儿等。”
苏康摆摆手,目光扫过县衙院子,只见里面的杂草比门口还疯长,都快长到膝盖高了,正堂门口的台阶缺了一块,露出里面的黄土,墙角堆着几捆没人收拾的枯枝,一片荒凉景象,比街上的铺子还破败。
没一会儿,瘦高个衙役就领着一个穿着青色官袍的中年人跑了出来。
那人约莫四十多岁,颔下三缕短须梳得整整齐齐,官袍虽然洗得白,却浆得平整,一看就是个爱体面的人。
他老远就拱手作揖,脸上堆满笑容:“苏大人远道而来,下官周文彬有失远迎,还望大人恕罪!”
苏康的年轻,让他愣了一下,
苏康上前一步回礼:“周县丞客气了,路上有些耽搁,昨日才到武陵,今日特来报到。”
“应该的,应该的!”
周文彬连忙侧身让开道路,眼睛却悄悄扫了眼苏康身后的马车,只见马车上堆着行李,没什么异样,才松了口气,“大人一路辛苦,快进里面歇息,下官已经备了薄茶。您的行李,让杂役先搬到后院的居所吧?下官早就让人把屋子打扫干净了,您直接住进去就行。”
“有劳周县丞了。”
苏康点点头,王刚立马会意,跟着过来的杂役去卸马车行李,那些连弩和炸雷藏得严实,杂役只当是普通衣物铺盖,也没多问。
周文彬引着苏康往里走,嘴里不停念叨:“咱们武陵虽不比京城繁华,却也算清静,春天有荠菜、苦菜,秋天能采野栗子、野山楂,就是今年天旱,收成差了些,百姓日子紧巴点……”
他只字不提瘟疫和政务,净捡些无关紧要的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