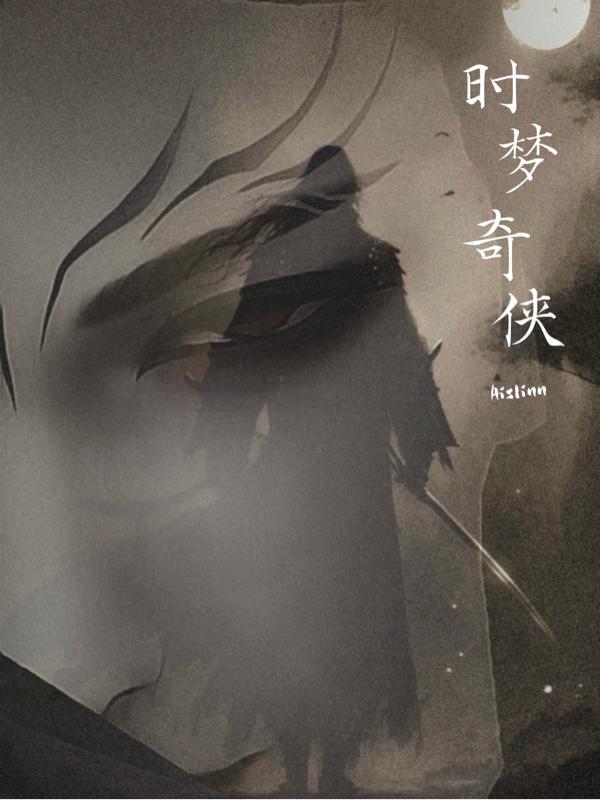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大乾风云起苍穹 > 第241章 冯铮亮的账册(第1页)
第241章 冯铮亮的账册(第1页)
县衙后堂的师爷房间里,烛火忽明忽暗。
冯铮亮手里攥着两本牛皮账册,指腹在磨得亮的封面上蹭来蹭去,心里头跟揣了只兔子似的,突突直跳。
窗外传来衙役巡逻的脚步声,他手忙脚乱地把账册塞进抽屉,后背紧紧抵住柜面,额角的汗珠子顺着皱纹往下淌,砸在褪色的官服前襟上。
三个多月前苏康刚到威宁那会儿,冯铮亮还以为自己这把老骨头要彻底歇菜了。
曹新把持县衙这些年,早就看他不顺眼,好几次都想把他踢走。直到那天苏康把聘书递过来,红纸上“特聘冯铮亮为威宁县衙师爷”几个字,他看了三遍才敢相信——自己居然还有被当人看的一天。
他当刑名师爷快二十年,跟着好几任县令熬过来,眼睁睁看着曹新和宋明这俩货把县衙变成自家后院,收税时往死里刮百姓,赈灾粮敢掺沙子,就连驿站的马料都要克扣。
他良心不安,夜里睡不着,就着油灯把这些腌臜事一笔一笔都记了下来,记满了两大本。
前院传来铁链拖地的哗啦声,冯铮亮撩开窗帘角瞅了眼,顿时吓了一大跳。
只见,曹新被俩衙役架着走,圆胖的脸白得像张纸,往日里那股子横劲儿全没了。宋明更惨,腿肚子打着颤,差点绊倒在门槛上,路过他窗根时,那眼神跟见了阎王爷似的,看得冯铮亮后脖颈子麻。
他缩回手,摸着抽屉里硬邦邦的账册,心里头在天人交战。
六年前户房的老李头,就是因为不肯在粮册上改数字,转年开春就“失足”掉进了护城河;捞上来时,手里还攥着半片被水浸透的账页。
现在把这东西交出去,自己那在西街接手书店的儿子,还有刚会走路的小孙子,能有好果子吃?
冯铮亮走到窗边,望着月光下黑沉沉的县衙飞檐。
檐角的铁马被风吹得叮当响,像极了苏康刚上任那天说的话:“冯先生,威宁这地方烂疮流脓,得找把敢下狠手的刀。我瞅着您就是这把刀。”
他想起苏康书房里那套《洗冤录》,书脊都磨破了,里面夹着不少苏康自己画的批注。
这位年轻县令跟以前那些官爷不一样,蹲在窑厂看匠人烧石灰能看到日头落山,在河堤上啃糙米饭比民夫还香,拿着他写的判词能逐字逐句问:“冯先生,这么判是不是太苛了?庄稼人过日子不容易。”
这样的官,值当赌一把。
冯铮亮深吸了一口气,从抽屉里掏出账册,用油布裹了三层,又塞进怀里贴肉的地方。冰凉的牛皮贴着心口,激得他打了个哆嗦。
摸了摸腰间的青玉佩,是老伴儿前年在观音庙求的,说能保平安。玉片子凉丝丝的,倒让他定了些神。
“去就去,大不了一条老命!”
他咬着牙嘀咕一句,撩起门帘就往后院走。
苏康的住处就在那儿,几间朴素的瓦房,门口就俩衙役在站岗。
“冯师爷?”
站岗的亲兵认得他,抬手行了个礼。
“劳烦通报,我有急事见苏大人。”
冯铮亮的声音有点紧。
没过片刻,柳青挑着灯笼出来了,脸上带着笑:“冯先生快请,大人正等着呢。”
书房里烛光明亮,苏康正低头看着卷宗,见他进来,立刻起身让座:“先生这时候过来,可是有要紧事?”
冯铮亮坐下,手在怀里摸了半天,才把油布包掏出来,搁在桌上推过去,指尖抖得厉害:“大人,曹新和宋明那俩货的底细,我这儿或许有些能用上的东西。”
苏康眉毛动了动:“哦?先生请讲。”
冯铮亮解开油布,露出两本泛黄的账册,纸页边缘都卷了毛边:“这是十年间记下的,曹新倒卖官粮,宋明偷库银的明细。哪年哪月,谁经手,收了多少好处,都在这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