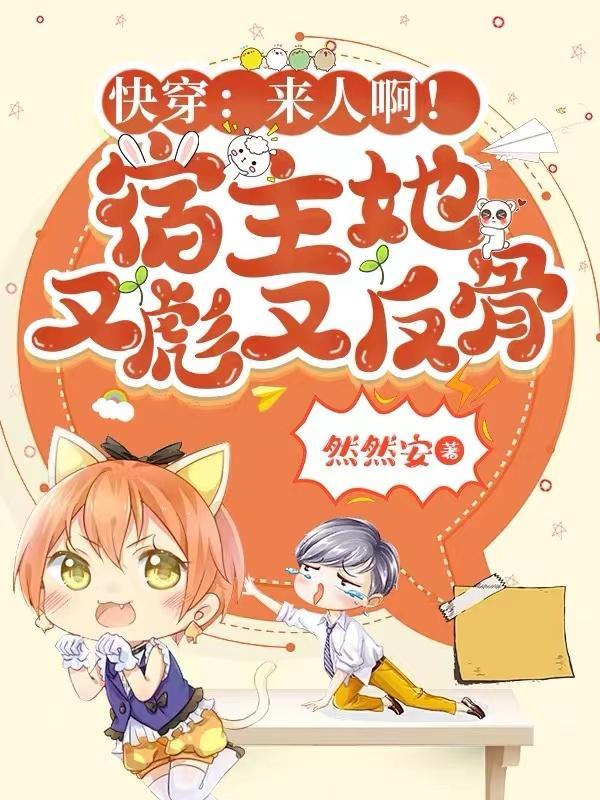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说好做任务怎么变成谈恋爱了?! > 第6章 人偶六(第1页)
第6章 人偶六(第1页)
随着人偶的四肢与躯干逐一完成,工作室的中心仿佛凝聚了一个无形的引力场。
秦晔停留在雕像前出神的次数明显增多了。
有时是端着水杯,目光却胶着在那空白的颈部上方,思绪不知飘向何方;
有时是深夜结束一部分工作后,他会洗净双手,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对着那无头的完美躯壳,一坐便是很久。
室内只有仪器运转的低沉嗡鸣,以及他自己时而平稳、时而紊乱的呼吸声。
他凝视着那属于神明的、完美而优雅的轮廓线条,仿佛能感受到某种内蕴的、非人的力量在玉石下搏动。
他的思绪纷乱芜杂,不再纯粹,夹杂着信仰的虔诚、艺术的偏执、乃至一丝近乎病态的迷恋。
如同嘈杂的电流,通过那无形的信仰纽带,源源不断地传递过去。
祂的困惑日益加深。
这个名为秦晔的信徒,实在古怪。
他并不像远古那些匍匐在祂座下的子民,虔诚地祈求风调雨顺、部落强盛、个人长寿或战役胜利。
那些欲望直接、鲜明,如同猎猎旌旗,易于理解。
而秦晔的“祈祷”,却总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那些关于“自我投射”、“审美认同”、“存在意义”的思考,在越看来,如同观察一团不断变幻形状、色彩迷离的迷雾。
还有那些偶尔闪过的、带着温度与隐秘渴望的念头,更是让这位神明感到费解。
秦晔这复杂、矛盾、甚至有些“不虔诚”的信仰,
反而像一种从未品尝过的、味道层次过于丰富的祭品,
让越感到困惑,却又并不讨厌。
对于一位古老的存在而言,信徒的思绪无论多么离奇,也只是河流中一朵稍显特别的浪花。
越依旧保持着沉默的观察。
祂只是偶尔,会在秦晔对着雕像出神,思绪最为混乱澎湃之时,
让那反哺回去的神力,带上一点点极其微弱的、安抚的韵律,
如同轻拍婴儿后背,让那躁动的灵魂能稍微平静下来,继续祂所期待的——“创造”。
秦晔闭上眼,最后一次在脑海中勾勒那张面容
——不是水中的倒影,不是梦中的幻象,而是属于的真正容颜。
玉石在他手下出细微的共鸣,像是沉睡的琴弦被悄然拨动。
他在雕刻时完全摒弃了凡俗的审美标准,而是执着地追寻着一种越形貌的。
当面部轮廓终于完成时,秦晔已经连续工作了整整两天。
他的眼底布满血丝,手指因为长时间握持刻刀而微微痉挛,但精神却异常亢奋。
现在,只差最后一步——镶嵌眼睛。
他取来了那对精心挑选、并已预先打磨成型的墨玉眼珠。
它们的色泽深沉如子夜,内部仿佛有星云在缓慢旋转,在工作室的灯光下,折射出幽玄的光泽。
就在他准备镶嵌的瞬间,一个突如其来的念头击中了他:
“当这双眼睛睁开,祂看到的会是什么?是虔诚的信徒,还是。……
一个借着造神之名满足私欲的狂徒?”
这个念头让秦晔的手僵在半空。
越第一次主动传递了一个清晰的意念——不是语言,更像是一阵微风拂过心间:
“完成它。”
秦晔猛地一震,几乎以为是自己出现了幻觉。
但那股来自心底的催促如此明确。
他的指尖因激动而微微颤抖,小心翼翼地将它们嵌入那精心雕琢的眼眶中。
“咔哒。”
一声极其轻微的、严丝合缝的嵌合声响起。
就在那一瞬间——仿佛沉睡的星辰被骤然点亮。
一股无形的、温和却不容忽视的“波动”以人偶头颅为中心,悄然荡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