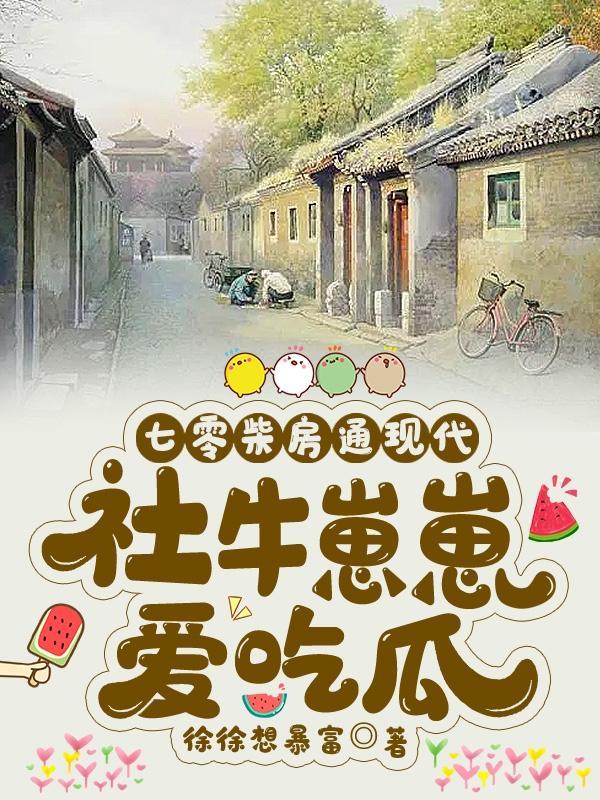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北军悍卒 > 第二百六十五章 戈壁与暗刃(第1页)
第二百六十五章 戈壁与暗刃(第1页)
风哭戈壁的风,名不虚传。
它不像镇北关的风那样是直来直去的猛牛,这里的风,更像是一把无形的,布满了锯齿的锉刀,从四面八方,不知疲倦地打磨着这片土地上的一切活物。
吴尽忠和他的一万禁军,已经在这把锉刀下,被磨了整整五天。
出征时的意气风,早已被吹得无影无踪。
那身在京城足以让百官侧目的亮银铠甲,如今成了最恶毒的刑具。
白天,它像一个铁笼,把太阳的毒辣尽数吸纳,蒸烤着里面的血肉之躯;
夜晚,它又变成了一块冰坨,贪婪地吸走身体里最后一丝热气。
“水……将军,水不多了。”副将的嘴唇干裂得像是被火烧过的树皮,声音嘶哑得几乎听不见。
吴尽忠看了一眼自己的水囊,那里面只剩下不到三口的量。
他舔了舔同样干裂的嘴唇,一股血腥味在口腔里弥漫开来。
“传令下去,每人每日,限水半囊。告诉弟兄们,再坚持一下,斥候来报,穿过前面那片沙丘,就能看到阿古拉的王帐了。”
这句谎言,他自己都不信。
五天了。
他们像一群没头的苍蝇,在这片一望无际的黄色炼狱里打转。
别说阿古拉的王帐,他们连一根蛮夷的毛都没看见。
斥候派出去几十波,带回来的消息永远是同一个:前方除了沙子,还是沙子。
队伍的士气,已经低落到了一个危险的临界点。
那些曾经在京城斗鸡走狗,以天子亲军自居的士兵,此刻一个个都成了蔫了的茄子。
他们歪歪斜斜地靠在骆驼上,眼神空洞,脸上的表情混合着疲惫、绝望和一种被愚弄后的愤怒。
他们开始怀疑了。
怀疑那个给他们指路的李琼,怀疑那个信誓旦旦的吴将军,甚至开始怀疑自己为什么要离开京城的安乐窝,跑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来送死。
“将军,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一名年轻的校尉,鼓起勇气问道。
他的脸上,还带着未脱的稚气,此刻却被风沙雕刻得满是沧桑。
吴尽忠的眼角抽搐了一下。
“放肆!”他厉声呵斥,声音却因为缺水而显得有些外强中干。
“军机大事,岂容你在此胡言乱语,动摇军心,再有下次,军法处置!”
那校尉被他一喝,缩了缩脖子,不敢再言语。
但吴尽忠知道,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就会在每个人的心里,疯狂地生根芽。
他看着这支曾经光鲜亮丽,如今却狼狈不堪的军队,心中第一次涌起一股彻骨的寒意。
他猛地想起了李琼。想起了那个年轻人在他出征前,为他斟酒时那张真诚的脸。
那张脸的背后,到底藏着什么?
吴尽忠不敢再想下去。
他怕自己会疯掉。
……
与吴尽忠的绝望不同,在距离风哭戈壁数百里之外的另一片草原上,李琼和他的一百名黑甲骑士,正像一群融入了夜色的狼,无声无息地穿行着。
他们没有骆驼,也没有笨重的辎重。
每个人都骑着两匹耐力极佳的草原马,轮换着骑乘,以保持最快的度。
他们的食物,是风干的肉条和炒熟的米粉,只需要一点水就能下咽。
他们的水源是沿途那些被斥候营提前标记好的,隐秘的地下泉眼。
李琼拉下面具,尝了尝风中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