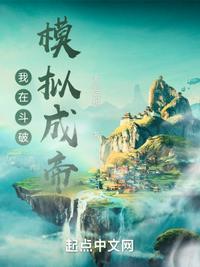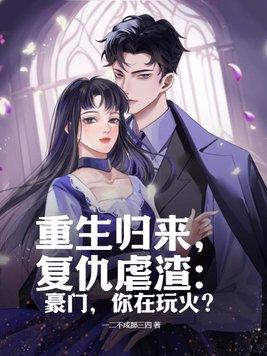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历史的回响:那些震撼人心的话语 > 第152章 中庸至德 久湮的中道之光(第1页)
第152章 中庸至德 久湮的中道之光(第1页)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孔子在杏坛讲授《诗》《书》时,见弟子们为“勇”与“怯”、“刚”与“柔”争论不休,放下手中的竹简长叹:“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秋日的阳光穿过梧桐叶,在弟子们的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这句感叹如同一颗投入深潭的石子,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激荡出绵延不绝的涟漪。中庸不是平庸的折中,而是“过犹不及”的智慧;不是随波逐流的妥协,而是“执两用中”的坚定。从孔门弟子的践行到当代人的追寻,这条“中庸”之路,始终是人类面对复杂世界的指南针,只是在漫长的岁月中,它的光芒常被极端与偏执所遮蔽。
一、中庸溯源:从“中”到“中庸”的思想演进
“中”的观念在中华文明中源远流长,远早于孔子的时代。殷墟甲骨文中的“中”字,像一面飘扬的旗帜,本义是“中央”“居中”,引申为“不偏不倚”的状态。《尚书?大禹谟》记载“允执厥中”,是舜传给禹的治国箴言,意为真诚地坚持中道;《周易?泰卦》“中以行愿”,《否卦》“大人否亨,不乱群也”,都蕴含着“中则吉,偏则凶”的朴素智慧。这些早期的“中”思想,为孔子“中庸”概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西周的礼乐制度,是“中”的理念在制度层面的体现。《周礼?天官?大宰》“以安邦国,以宁万民,以怀宾客”,强调治国需“和而不同”;《礼记?乐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认为礼乐的本质是“和序相济”,避免过与不及。周公制礼作乐时,既反对殷商的酗酒淫逸(过),又不赞同过度禁欲(不及),而是“制礼以节事,作乐以导志”,这种“节”与“导”的平衡,正是“中”的实践。
春秋时期的晏婴,以“和而不同”诠释了“中”的内涵。他在回答齐景公“和与同异乎”时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认为真正的和谐如同调味,需“济其不及,以泄其过”,而非简单的同一。晏婴还以君臣关系为例:“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这种既不盲从又不固执的态度,正是“中”的智慧,对孔子中庸思想的形成有直接影响。
孔子将“中”与“庸”结合,提出“中庸”概念,使其从朴素的平衡观念升华为系统的道德哲学。“庸”在《说文解字》中为“用也”,“中庸”即“用中”,将“不偏不倚”的原则应用于日常实践。他说“过犹不及”(《论语?先进》),以子张的“过”与子夏的“不及”为例,说明二者同样偏离正道;又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强调中庸不是无原则的调和,而是在差异中寻求和谐。这种思想的创新在于:它将“中”从外在的行为规范内化为“德”的核心,成为君子修身的最高境界。
二、中庸之德:过犹不及的智慧刻度
中庸的核心是“过犹不及”,这一智慧刻度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体现。饮食上,“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论语?乡党》)是对品质的追求,而“不多食”“酒不及乱”则是对节制的坚守,二者结合便是饮食上的中庸;言行上,“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是对“言过其实”的警惕,“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是对“行不及言”的纠正,平衡二者便是言行上的中庸。这种“度”的把握,是中庸最难也最珍贵的地方。
在政治领域,中庸表现为“宽猛相济”的治理艺术。孔子在评论郑国子产的治国方略时说:“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子产临终前告诫继任者子大叔“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正是对中庸之道的践行。春秋时期的齐国,管仲既推行“相地而衰征”的改革(猛),又实行“通货积财,富国强兵”的富民政策(宽),使齐国“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展现了政治中庸的成效。
在个人修养上,中庸体现为“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述而》)的人格特质。孔子本人便是这种特质的典范:他对待弟子“因材施教”,对子路的“过”加以约束,对冉有的“不及”加以鼓励;他周游列国时,既“危行言逊”以避祸,又“知其不可而为之”以行道;他评价人物,既肯定管仲的“如其仁”,又批评其“器小”,这种全面辩证的态度,正是中庸的人格化。
中庸还意味着在原则与权变之间找到平衡。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权”即通权达变,是中庸的高级形态。“嫂溺,援之以手”(《孟子?离娄上》)的典故,生动诠释了这种权变:“男女授受不亲”是常规原则(经),“嫂溺援之以手”是特殊情况下的权变(权),二者都是中庸的体现,因为它们都符合“义”的根本要求。
三、民鲜久矣:中庸失落的历史轨迹
孔子感叹“民鲜久矣”,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对春秋时期中庸之道逐渐失落的敏锐洞察。周平王东迁后,“礼崩乐坏”,诸侯争霸,大夫专权,整个社会陷入“过”与“不及”的极端:晋献公“骊姬之乱”废长立幼(过),齐桓公晚年任用奸佞(过),宋襄公“泓水之战”迂腐守礼(不及),这些都是偏离中庸的典型案例,孔子目睹了这一切,才出如此深沉的感叹。
战国时期,中庸之道进一步被边缘化。诸子百家虽各有建树,却多走向极端:墨子“兼爱”“非攻”,否定差序之爱(不及);杨朱“为我”“贵己”,否定社会责任(过);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否定道德教化(过);道家“绝圣弃智”“小国寡民”,否定文明进步(不及)。孟子批评“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正是对这种极端化倾向的批判。
秦汉时期,中庸思想在实践中遭遇曲折。秦始皇“焚书坑儒”“严刑峻法”,是“过”的极致;汉初“无为而治”,虽一度恢复生机,却导致诸侯坐大(七国之乱),是“不及”的表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看似推崇儒家,实则“外儒内法”,将中庸异化为“霸王道杂之”的权术,失去了其“至德”的本质。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将“中”神秘化为“天之道”,却在实践中沦为谶纬迷信的工具。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盛行,放达之风取代了中庸。“竹林七贤”追求“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阮籍“礼岂为我辈设也”,这种对礼教的极端反抗,是对“过”的另一种演绎;而佛教的传入,虽带来新的思想资源,却也导致“因果报应”“出世修行”等观念盛行,与中庸的“入世”精神形成张力,进一步加剧了“民鲜久矣”的局面。
唐宋时期,中庸思想虽有复兴,却仍未完全回归本真。韩愈倡导“古文运动”,试图重振儒家道统,却过于强调“排佛老”的极端;程朱理学将“中庸”纳入“天理”体系,“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虽强调“中”,却带有禁欲主义色彩(过);陆王心学主张“心即理”,虽重视内在觉悟,却有时忽视外在规范(不及)。这种理论上的偏颇,使中庸之道始终未能真正深入人心。
明清时期,中庸逐渐沦为“乡愿”的代名词。《论语?阳货》中孔子批评“乡愿,德之贼也”,乡愿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的伪君子,与真正的中庸有本质区别。明清官场的“和稀泥”“打圆场”,民间的“不得罪人”“明哲保身”,都是对中庸的误解与异化。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批判宋明理学“以理杀人”,正是看到了这种伪中庸对人性的压抑。
四、孔门践行:弟子们的中庸探索
孔门弟子中,颜回最得中庸精髓,却“不幸短命死矣”(《论语?先进》)。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在贫困中保持安和(中);他“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对孔子的教诲既不盲目服从(过),也不轻易质疑(不及);他问仁时,孔子答“克己复礼为仁”,他能领悟“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中庸内涵,这种“闻一知十”的悟性,使他成为孔门中最接近中庸的弟子。
子贡以言语见长,在经商与行道中践行中庸。他“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先进》),经商时既追逐利润(不过),又“富而无骄”(非不及);他出使列国时,既“辩才无碍”以成事(不过),又“出使不辱君命”以守礼(非不及);他评价孔子“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既推崇师道(不过),又不神化夫子(非不及),这种平衡的智慧,使他成为孔门中践行中庸的佼佼者。
子路的性格虽“行行如也”(《论语?先进》),有“过”的倾向,却在孔子的教导下逐渐趋近中庸。他在卫国为官时,既“片言可以折狱”(《论语?颜渊》)以行刚,又“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论语?公冶长》)以行柔;他在“蒯聩之乱”中,既“食其食者不避其难”以尽忠(不过),又“君子死,冠不免”以守礼(非不及),最终“结缨而死”,用生命诠释了中庸的“守经达权”。
冉有长于政事,在施政中体现中庸。他为季氏宰时,既“为之聚敛而附益之”(《论语?先进》)以满足大夫需求(不过),又“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论语?八佾》),虽未能阻止季氏僭礼,却也未助纣为虐(非不及);他随孔子周游列国时,在陈绝粮仍“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论语?先进》),保持镇定,这种“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论语?述而》)的态度,正是政事中的中庸。
五、中庸与异端:中外思想的对话
中庸思想并非中华文明独有,在世界其他文明中也有类似的智慧,只是表述不同。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提出“中道学说”,认为“德性是一种适度,因为它以居间者为目的”,勇敢是怯懦(不及)与鲁莽(过)的中道,节制是放纵(过)与禁欲(不及)的中道,这种思想与孔子的“过犹不及”惊人地相似,只是亚里士多德更注重逻辑论证,孔子更强调实践智慧。
佛教的“中观”思想,与中庸有相通之处。龙树菩萨在《中论》中提出“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反对“有”与“无”的极端,主张“诸法空相”的中道,这种对二元对立的越,与中庸的“执两用中”有精神上的契合。但佛教的“中”更偏向出世的解脱,儒家的“中庸”更注重入世的践行,这是二者的本质区别。
道家的“守中”思想,与中庸既有联系又有差异。《老子》“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主张在“有无相生”“难易相成”的辩证关系中保持中道;《庄子》“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强调顺应自然的“中”。但道家的“中”带有消极避世的色彩(不及),儒家的“中庸”则是积极入世的担当,正如孔子所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虽有避世之语,实则始终以行道为己任。
基督教的“中庸之道”,体现在对“节制”的强调。《圣经》中“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nets1o:23》),与“过犹不及”的思想相通;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反思自己年轻时的纵欲(过)与后来的苦行(过),最终领悟到“爱上帝并爱人如己”的中道。但基督教的“中”以“爱上帝”为前提,儒家的“中庸”以“仁”为核心,前者带有宗教色彩,后者更具人文精神。
这些中外思想的对话表明,中庸是人类共同的智慧追求,只是在不同文化语境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孔子将中庸视为“至德”,正是看到了它对于处理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普适价值,这种价值在全球化的今天,更显其跨越时空的生命力。
六、中庸的现代误读:平庸与乡愿的混淆
在当代社会,中庸常被误解为平庸、妥协、不作为的同义词,这种误读使“民鲜久矣”的状况进一步加剧。有人将“中庸”等同于“差不多先生”的敷衍了事,做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有人将“中庸”看作“和事佬”的和稀泥,遇到矛盾“各打五十大板”;有人将“中庸”理解为“随大流”的盲从,“别人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这些都与孔子所说的“中庸”相去甚远,它们是“乡愿”的现代变种,是“德之贼也”。
平庸与中庸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有“德”的支撑。中庸以“仁”为核心,“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是对“礼”与“仁”的坚守;平庸则缺乏内在的价值准则,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浑浑噩噩。北宋的王安石变法,虽有“过”的倾向,却出于“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改革担当,比那些“因循守旧、苟且偷安”的平庸之辈更接近中庸的精神;明代的海瑞,虽“过刚”,却“抬棺死谏”以纠时弊,其“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勇气,远比“明哲保身”的乡愿更有价值。
乡愿与中庸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有原则立场。乡愿“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孟子?尽心下》),表面上“左右逢源”,实则毫无原则;中庸则“君子和而不同”,在坚持核心原则的前提下,与不同意见保持和谐。当代职场中,有人为了晋升“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乡愿),有人则“坚持原则,灵活沟通”(中庸);网络空间中,有人“键盘侠”式的极端批判(过),有人“好好先生”式的无原则点赞(不及),都不是中庸的表现,真正的中庸是“理性表达,尊重差异”。
中庸的现代误读,还源于对“中”的机械理解。有人认为“中”就是“一半对一半”的折中,如在“好”与“坏”之间取“不好不坏”,在“对”与“错”之间取“模棱两可”,这种数学意义上的“中”,失去了中庸的精神内核。真正的中庸是“义之与比”(《论语?里仁》),根据“义”的要求灵活调整,有时需要偏向“刚”(如面对不公),有时需要偏向“柔”(如处理人际关系),正如孟子所说“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孟子?尽心上》),没有权变的“中”,不是真正的中庸。
七、当代回响:中庸智慧的现实价值
在价值多元、矛盾频的当代社会,中庸之道的现实价值愈凸显。它为个人处理人际关系提供了准则——既不过分亲密而失去边界,也不过分疏远而显得冷漠;为企业管理提供了方法——既不过度集权而扼杀活力,也不过度分权而导致混乱;为国家治理提供了思路——既不过度干预市场(过),也不放弃宏观调控(不及);为国际关系提供了原则——既坚持国家主权(刚),又倡导合作共赢(柔)。这种“执两用中”的智慧,是应对复杂挑战的有效工具。
在个人成长方面,中庸表现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的全面展。现代教育过于强调分数(过),忽视品德培养(不及),而中庸的教育观主张“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现代人常陷入“工作狂”(过)与“躺平族”(不及)的极端,而中庸的生活态度是“奋忘食,乐以忘忧”(《论语?述而》)与“食不言,寝不语”(《论语?乡党》)的平衡,既积极进取,又懂得休息。
在环境保护领域,中庸体现为“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工业文明时期“征服自然”的观念(过)导致生态破坏,后工业时代的“反展”思潮(不及)不符合现实需求,而中庸的生态观主张“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礼记?王制》),如中国推行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既不放弃展(非不及),又不牺牲环境(非过),正是“执两用中”的实践。
在科技伦理方面,中庸表现为“科技向善”的价值导向。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新技术的展,既不能因恐惧风险而停滞创新(不及),也不能为追求进步而忽视伦理(过),中庸的态度是“兴利除弊”——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建立健全伦理规范,正如孔子所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工具的进步需要与价值的坚守相平衡。
这些当代实践表明,中庸不是过时的教条,而是与时俱进的智慧。它不排斥创新与变革,而是主张在传承与创新之间找到平衡;它不否定个性与差异,而是倡导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实现和谐。孔子所说的“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在今天依然成立,因为它触及了人类生存与展的根本问题。
八、重燃中道之光:让中庸回归生活
让中庸之道重放光芒,需要从教育入手,还原其“至德”的本真内涵。在中小学教材中,应增加对“中庸”的正确解读,区分中庸与平庸、乡愿的区别;在大学课程中,应开设“中庸思想研究”等课程,探讨其与现代社会的结合点;在家庭教育中,父母应以身作则,在“严”与“慈”之间找到平衡,培养孩子的中庸意识。只有让年轻一代真正理解中庸,才能改变“民鲜久矣”的状况。
让中庸之道落地生根,需要在制度层面提供保障。企业应建立兼顾效率与公平的薪酬体系,避免“996”的极端加班(过)与“大锅饭”的平均主义(不及);政府应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既保障基本民生(非不及),又避免养懒人(非过);社会应建立多元评价体系,打破“唯分数、唯学历、唯职称”的单一标准(过),让不同特质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中”。
让中庸之道深入人心,需要每个人在生活中践行。面对网络言论,既不盲目跟风(过),也不漠然旁观(不及),而是理性表达;面对工作压力,既不消极应付(不及),也不透支健康(过),而是劳逸结合;面对人际关系,既不阿谀奉承(过),也不孤高自傲(不及),而是真诚待人。这种“日用而不知”的践行,比空洞的理论宣传更有效。
九、中庸不朽:人类永恒的精神追求
孔子的“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穿越两千五百年的时空,依然在叩问着每个时代的人们。中庸不是教条的公式,而是活的智慧;不是过去的遗迹,而是未来的指南。它在历史的长河中时隐时现,却从未真正消失,因为它扎根于人性的深处——对和谐的渴望,对平衡的追求,对极端的警惕。
从“允执厥中”的舜禹之道,到孔子的“过犹不及”,从子产的“宽猛相济”,到当代的“和谐社会”,中庸之道如同一条隐秘的红线,贯穿中华文明的始终。它告诉我们:人类的进步不在于极端的突破,而在于平衡的智慧;社会的和谐不在于消除差异,而在于差异中的和谐;个人的完善不在于偏执的追求,而在于全面的展。
或许,“民鲜久矣”的状况难以在短期内彻底改变,但只要有人在践行中庸,有人在传承其精神,这束“至德”的光芒就不会熄灭。当我们在生活中多一分克制,少一分放纵;多一分理解,少一分偏执;多一分平衡,少一分极端,就是在接近中庸,就是在回应孔子的感叹。
中庸不朽,因为它是人类面对复杂世界的永恒智慧;中庸可期,因为它存在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让我们以孔子的“中庸”为镜,在各自的生活中寻找属于自己的“中”,让这束久湮的中道之光,重新照亮人类前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