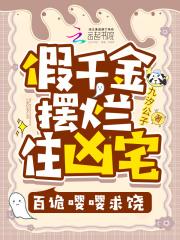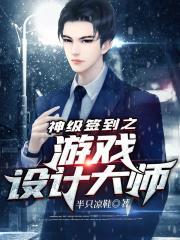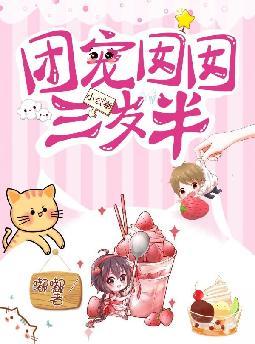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历史的回响:那些震撼人心的话语 > 第138章 不伐之德 孟之反的君子风度(第1页)
第138章 不伐之德 孟之反的君子风度(第1页)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
一、鲁军奔退中的那抹亮色
鲁哀公十一年的秋天,齐国的军队撤退了,鲁国的都城曲阜城外,弥漫着战后的疲惫与混乱。败兵们丢盔弃甲,争先恐后地涌向城门,尘土飞扬中,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惊恐与狼狈。就在这溃败的洪流里,有一个身影显得格外不同——孟之反。
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只顾着逃命,而是勒住缰绳,掉转马头,殿后掩护。手中的马鞭轻轻拍打马背,目光却始终扫视着身后,确保没有掉队的士兵被齐军追上。当最后一名鲁军士兵踉跄着进入城门,孟之反才策马跟上。守城的士兵看到他,纷纷投来敬佩的目光,有人忍不住喊道:“孟大夫,您殿后辛苦了!”
孟之反听到喊声,却没有丝毫得意。他在马上微微侧身,举起马鞭指了指自己的马,笑着说:“非敢后也,马不进也。”——不是我敢于殿后,是这匹马不肯往前走啊。
这句看似轻松的话,被恰好路过的孔子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后来,孔子在给弟子们讲学的时候,特意提起这件事,赞叹道:“孟之反不伐。”——孟之反不夸耀自己的功劳。
这个生在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场景,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没有慷慨激昂的誓言,却因孟之反这句看似平淡的话,成为了儒家典籍中关于“不伐”之德的经典范例。它像一粒种子,在后世的土壤里生根芽,长成了中华民族崇尚谦逊、不事张扬的精神大树。
二、“伐”的多重面相:从自我夸耀到品德迷失
要理解孟之反的“不伐”之德,先需要认清“伐”的本质。“伐”在古汉语中本义为“砍伐”,引申为“夸耀、自夸”,《说文解字》解释为“击也”,段玉裁注“引申为自矜”。在儒家看来,“伐”不仅仅是一种言语上的炫耀,更是一种内心的品德迷失,它会让人偏离“中庸”之道,陷入傲慢与浅薄的泥潭。
“伐”的第一种面相是居功自傲。即对自己的功劳沾沾自喜,四处宣扬,甚至贬低他人以抬高自己。《论语?公冶长》中记载,子贡问孔子:“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子贡虽然得到了孔子的肯定,却没有因此夸耀,而有些人一旦做出一点成绩,就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这种“伐”会让人失去清醒的自我认知。
“伐”的第二种面相是好大喜功。即做事情不是为了实际效果,而是为了追求名声,喜欢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义。历史上很多帝王将相,为了彰显自己的功绩,大兴土木,动战争,导致民不聊生,如秦始皇修建阿房宫、汉武帝连年征战,虽然留下了一些“功绩”,却也给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这种“伐”会让人为了虚名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伐”的第三种面相是嫉贤妒能。即不能容忍别人比自己优秀,看到别人有功劳就嫉妒,甚至想方设法诋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记载,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却因上官大夫的嫉妒而被楚怀王疏远,最终投江自尽。这种“伐”会破坏人际关系,阻碍团队的展,是一种非常恶劣的品德。
“伐”的第四种面相是虚伪做作。即通过虚假的言行来夸耀自己,装作很有功劳或品德高尚的样子,实际上却名不副实。《论语?阳货》中记载的“乡原,德之贼也”,就是指那些看似忠厚老实,实则虚伪狡诈的“好好先生”,他们通过讨好别人来获得好名声,这种“伐”比直接的夸耀更具迷惑性,对品德的破坏也更大。
“伐”的这四种面相,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本质上都是以自我为中心,过分看重名利,忽视他人和集体的利益。它们会像蛀虫一样,侵蚀人的品德,破坏社会的和谐,因此儒家将“不伐”视为君子的重要品德。
三、孟之反“不伐”的深层内涵:谦逊背后的精神境界
孟之反的“不伐”,绝不仅仅是一种言语上的谦虚,而是一种深刻的精神境界,它包含了对自我、对功劳、对他人的清醒认知,体现了儒家“仁”“义”“礼”“智”等核心价值观的统一。
先,“不伐”是对自我价值的正确认知。孟之反知道,自己殿后虽然起到了掩护作用,但这是作为大夫的职责所在,不值得夸耀。他没有把自己看得过高,也没有把功劳都归于自己,而是客观地看待自己的行为。这种自我认知,是“智”的体现——知道自己的位置和能力,不盲目自大。正如《论语?学而》中孔子所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君子不会因为别人不了解自己的功劳而生气,因为他们对自己的价值有清晰的认知,不需要通过别人的称赞来证明。
其次,“不伐”是对功劳本质的深刻理解。孟之反明白,一场战争的胜负,一个团队的成败,不是某一个人的功劳,而是集体努力的结果。他殿后之所以能成功,离不开士兵们的配合,离不开守城将士的接应,甚至离不开齐军的撤退。把功劳归于自己,是对集体努力的忽视。这种对功劳本质的理解,是“义”的体现——知道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争的,懂得尊重集体的利益。正如《周易?系辞上》所说“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有功劳却不夸耀,是深厚品德的体现。
再次,“不伐”是对他人感受的尊重与关怀。孟之反在败军之际殿后,已经显示了自己的勇敢和担当,如果再夸耀自己的功劳,会让那些逃跑的士兵感到羞愧和难堪,不利于军队的团结。他用“马不进也”的借口,既掩饰了自己的功劳,也给了其他士兵台阶下,体现了对他人感受的细腻关怀。这种关怀,是“仁”的体现——爱人如己,懂得体谅他人的处境。正如《论语?颜渊》中孔子所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之反不希望自己的夸耀给别人带来不适,所以选择了谦逊。
最后,“不伐”是对“礼”的自觉践行。儒家强调“礼”,认为“礼”是调节人际关系的规范,而谦逊是“礼”的重要组成部分。《礼记?曲礼上》说“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孟之反的“不伐”,正是对这种“礼”的自觉遵守。他用温和的语言和态度,避免了因夸耀而可能引起的冲突和不满,维护了人际关系的和谐。这种对“礼”的践行,体现了君子的修养和风度。
孟之反“不伐”的深层内涵,是自我认知、集体意识、他人关怀与礼仪修养的有机统一。它不是一种刻意的伪装,而是一种自内心的品德自然流露,是君子人格的生动体现。
四、孔子眼中的“不伐”之德:儒家君子的重要标准
孔子对孟之反“不伐”的称赞,不是偶然的,而是与他对君子品德的整体要求相一致的。在孔子看来,“不伐”是君子必须具备的重要品德,它与“仁”“义”“礼”“智”“信”等品德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君子的人格体系。
孔子在《论语》中多次强调“不伐”的重要性。他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君子没有什么可争的,如果有的话,就是射箭比赛了。比赛时,互相作揖谦让后上场,比赛结束后互相敬酒,这种竞争才是君子的竞争。这里的“无所争”,就包含了“不伐”的意思——不与他人争夺功劳和名声。
孔子还说:“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论语?雍也》)这是对孟之反“不伐”行为的直接称赞,表明孔子将这种行为视为君子的典范。在孔子看来,君子应该像孟之反这样,有功劳却不夸耀,保持谦逊的态度。
孔子之所以如此重视“不伐”之德,是因为它符合儒家“中庸”的思想。“中庸”是儒家的重要理念,指的是不偏不倚、恰到好处的状态。“伐”是一种极端的行为,表现为过度的自我夸耀;而“不伐”则是一种中庸的态度,既不夸耀自己,也不贬低自己,恰到好处地看待自己的功劳和能力。
“不伐”之德也与孔子“克己复礼为仁”的思想相呼应。“克己”就是克制自己的欲望和情绪,“复礼”就是遵守礼仪规范。“伐”往往源于过度的欲望(如名利欲)和情绪(如骄傲),而“不伐”则是“克己”的结果,是对自己欲望和情绪的有效克制,从而达到“复礼”的境界,最终实现“仁”的目标。
在孔子看来,具备“不伐”之德的君子,能够更好地处理人际关系,促进团队的和谐与合作。因为不夸耀自己,所以能够尊重他人;因为不争夺功劳,所以能够团结他人;因为保持谦逊,所以能够学习他人的长处。这样的君子,才能成为他人的榜样,才能承担起治理国家、教化百姓的责任。
孔子眼中的“不伐”之德,不是一种消极的退缩,而是一种积极的进取。它要求君子在有功劳时保持谦逊,同时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勇于担当。正如孟之反在败军之际敢于殿后,体现了他的担当精神;而在事后不夸耀,体现了他的谦逊品德。这种“担当”与“谦逊”的统一,才是完整的“不伐”之德。
五、历史上的“不伐”典范:从古代到近代的品德传承
孟之反的“不伐”之德,为后世树立了榜样,历史上涌现出了许多“不伐”的典范,他们用自己的行为诠释了“不伐”的内涵,传承了儒家的君子品德。
卫青的“功高不伐”:西汉名将卫青,多次率军抗击匈奴,立下了赫赫战功,被封为大司马大将军。但他从不夸耀自己的功劳,待人宽厚,与士兵同甘共苦。有一次,汉武帝赏赐给他千金,他却拿出一半赏赐给了部下。有人劝他应该彰显自己的功劳,卫青却说:“我能有今天的成就,全靠陛下的信任和将士们的努力,我怎么能独自夸耀呢?”卫青的“功高不伐”,让他赢得了部下的爱戴和百姓的尊敬,成为历史上着名的贤将。
范仲淹的“先忧后乐”:北宋名臣范仲淹,一生忧国忧民,推行庆历新政,为国家和百姓做了很多好事。但他从不夸耀自己的政绩,始终保持谦逊的态度。他在《岳阳楼记》中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表达了自己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却没有一句提及自己的功劳。有人称赞他的功绩,他总是说:“这是我应该做的,没有什么可夸耀的。”范仲淹的“不伐”,体现了他“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和谦逊的品德。
曾国藩的“功成不居”:晚清重臣曾国藩,率领湘军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为清朝的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他深知“功高震主”的道理,始终保持低调,不夸耀自己的功劳。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总是将功劳归于皇帝的英明和将士的奋勇,从不突出自己的作用。平定太平天国后,他主动裁撤湘军,表明自己没有野心。曾国藩的“功成不居”,体现了他的政治智慧和谦逊品德,也让他得以善终。
钱学森的“国为重,家为轻”:近代科学家钱学森,放弃美国的优厚待遇,回国后为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但他从不夸耀自己的功劳,总是把成就归于集体。有人称他为“国宝”,他却说:“我只是沧海一粟,真正的功劳属于国家和人民。”钱学森的“不伐”,体现了他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以及谦逊的科学家精神。
这些“不伐”的典范,虽然身处不同的时代,从事不同的职业,但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有功劳却不夸耀,始终保持谦逊的态度,将功劳归于集体或他人。他们的行为,不仅传承了孟之反的“不伐”之德,也丰富了儒家君子品德的内涵,为后世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六、“不伐”与“自矜”的博弈:人性中的永恒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