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五小说网>明末:我为大明延寿七百年 > 第258章 制定长期国策(第3页)
第258章 制定长期国策(第3页)
朱由检一高兴,说着就要批准。
“陛下且慢,臣有话说。”
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张书缘是赶忙起身阻止。
“哦?张爱卿是有何话?难道毕阁老之策有误?”
“陛下,毕阁老之策无误,但却有几处弊病,一是此法易滋银数短少,成色参差。二是容出虚报冒支,无册可核。三是此法易使边商内商层层倒卖,坏我盐法。”
轰的一下,这所有人便就冷静了下来。
是啊,这法子虽然是能省钱,但却也是破坏了原有的账册规制,一旦有了急用钱的大事,或是朝廷要追查地方用度时,就没法再用查账簿这个办法了,因为没有了实物参照,那便就有了虚报的空间。
“张阁此言…倒也为实。陛下老臣是一时心急差点致我朝于危险之境,还请陛下责罚!”
毕自严不愧是才学大儒,在想明白后完全就没有生张书缘的气,反而是被这说法给吓了一跳。
也是,他这办法的弊处,还是在施行了三年后才被他自己给现的,而当时他也给出了解决办法,那便就是造册登记、兑支监督以及盐引对号截角。
“诶,毕爱卿也是为我朝大事也操心,有此失误也在情理之中,况且毕爱卿之法,也未曾施行算不得有罪。”
朱由检是呵呵笑着摆了摆手,在他看来若那满朝文武都似毕自严这般该多好,但奈何除去他毕自严外,还真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到为朝廷开源节流的。
“张爱卿,既然你说阁老之策有弊,那你可有谏言消弭此弊?”
虽然大概率知道小哥有办法,但他还是想听听小哥会说出什么惊人之语。
“陛下,若要臣说,臣的办法是,我朝可改举赋税运输之法。将原先由各县府道调拨京师的钱粮,统改为统收统支。”
“哦?统收统支?”
说实在的,就眼下的生产力而言,根本没法像后世那样,叫钱在账上走,说到底还是要进行长途的实物运输。
“陛下,这所谓的统收统支,便是指将各县赋税集中到清吏司之后,等造编成册后,再由司员将其押送到省府的太仓,最后再由布政司按户部调令统一起运进京,或协拨他省,或存留本省用于官俸、兵饷等支出。”
“若遇急需,则我户部可下拨法令一道,使其将库银调往指定口岸或军前,而如此便可省去大量的运输费用了。”
张书缘虽然不像毕自严那般善于计算,但他却知道眼下的根本是在于运输,而一年下来朝廷至少要花二十多万两在运输之事上。
“好主意啊,层层建册,一旦查起也好追根溯源!”
张书缘这话一出,温体仁与毕自严瞬间就眼前一亮。
“除了此举之外,臣还在毕阁老之言上,加四法。一乃当场验银、三方会签。二乃建立军册多报,递送御前与户部核验。三乃盐随引走,在盐引之上留作符印及缺口。四乃银盐两账,按日滚存!”
听完这最后一句话,所有人顿时就对张书缘佩服了起来。
说实话,眼下的他们这群人,大多数都是困在了那些条条框框之中,很善于将简单的事情给复杂化。
但张书缘却不同,他很明白各司其职和化繁为简的道理,而在后世莫说是国家大事了,就是一小公司也都要分列单册。
“好,张爱卿果然乃我天选之臣,此事就以张爱卿所言处置吧。毕爱卿负责改制之事,待挤出银钱之后再调拨于兵部大兴新军编造。”
朱由检是高兴极了,当即就准了这一套说法。
“臣领旨。”
毕自严摸了摸鼻子,转而便就令下了这份差事。
就这样,众人围绕着财、权、军三项大事,很快就定出了以下几个长期国策。
一、改革赋税运输,不再由各道各县起运,改为由十三府布政司负责。
二、待天津试点无误后,将大力推行新商法及土地丈量于全国,待事成之后,立即启用“官绅一体纳粮”之策。
三、编造新军,裁汰冗员,将在册的全国官员总数控制在五万左右。
四、在辽东推行蚕食之法,依托大陵城向辽东深处渗透。
五、加大航海贸易,出使域外他国。
六、加大力度赈灾安抚灾民,并下恩典准许商贾以雇佣流民之事,减免其三成税赋。
七、户部要立即开展黄册革新之事,着重统计伤亡灾民及百姓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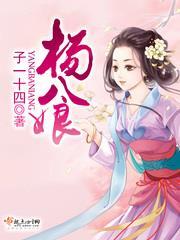
![自我救赎很难吗?[快穿]+番外](/img/352058.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