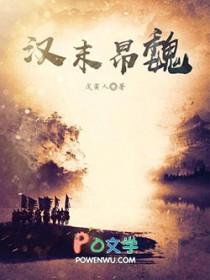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三国:我,曹操长子,开局屠司马 > 第552章 往最需要驻军之处去即可(第3页)
第552章 往最需要驻军之处去即可(第3页)
朱松笑着点头。
“四哥想问你,关于藩王不可世袭的规定,是父皇的主意,还是你的提议?”朱棣紧盯着朱松问道。
朱棡和朱权的脸色微变,深知此问题若回答不当,朱松恐将遭众藩王非议。
但在他们看来,此等大事定由父皇决断,岂容藩王置喙?
朱松洞悉朱棣之意,连忙摇头:“四哥多虑了,父皇的决定,岂是我能左右的?”
“那你所知应比我们更多。”朱棣继续追问,“若我们不在,燕王的封号与北平府的封地是否会随之消失?”
“自是如此。”朱松肯定道,“不仅四哥,所有藩王皆同。”
“父皇之意,日后欲就藩,须凭实力。”
“藩位能者居之。”朱松微笑点头。
朱棣、朱棡、朱权皆露恍然大悟之色,此事显非朱松所能定,必是父皇之意。
藩王不世袭,封号封地收回自是顺理成章。
“漠北已平,我们回朝后,兵权是否也会被朝廷收回?”朱棣问出了心中所忧。
朱棡和朱权闻言色变,此问题他们未曾深思。
但朱棣一提,他们顿时醒悟。
九边重镇重兵囤积,藩王镇守,不正是为御北方之敌?如今北方无忧,重兵是否还有必要?
“四哥所言极是!”朱松应道。
漠北平息后,北方藩王的兵权将渐次回收,因无需再维持庞大军力。
朱松点头,对此解释,朱棣等人无从反驳。
敌人已除,何需重兵?莫非别有他图?
朱松情形特异,其兵权非但不会削弱,反而增强。
因汉中军需镇守西域广袤之地。
漠北虽安,西域诸国如帖木儿汗国等,仍与漠北关联密切,乃大明重点防范对象。
朱棣面色阴沉,此结果他早有预料,但从朱松口中证实,便成定局。
兵权将削,他难以接受。
北方无忧,燕王军乃至朝廷军或北移漠北,毕竟漠北军事要塞与城池众多,非虚设。
九边重镇兵力北迁,可预见也。
朱棡与朱权初感震惊,旋即冷静。
二人无野心,兵权有无皆无所谓。
唯朱棣心生不快。
“四哥怕父皇收回兵权?”朱松笑问,“九弟有一计,非但保你兵权不失,反能壮大实力。”
朱棣脸色微变,未料朱松主动献策保兵权,增实力。
“何计?”朱棣问。
“简单,往最需要驻军之处去即可。
四哥之子日后亦将封于漠北,若四哥同往……”
朱松言犹未尽,其意已昭然若揭:意在促使朱棣自选迁往漠北受封。
迁漠北,兵权犹在;留北平,兵力必削,恐仅存万余,乃至更少。
闻此,朱棣愕然立定,未料此为一选择题!
又,时值凯旋,徐妙锦有孕,乃朱匣焌之二胎。
朱棣面临抉择:北平或兵权。
北平留,兵权失,老爷子必削兵,无大敌,何需重兵?朝廷可名正言顺收兵权,仅余万余护卫。
若选兵权,依朱松言,唯迁漠北一途。
大明需驻军之地,北乃漠北,南为云南,西则西域。
朱棣之选,唯漠北耳。
西域无望,云南漠北,南北相隔,岂能与子分散?若朝廷防线北移至漠北,朱棣迁漠北,亦顺理成章,唯在其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