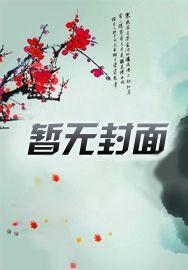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不第河山 > 第401章 金明池畔暗流涌(第1页)
第401章 金明池畔暗流涌(第1页)
皇佑元年的春日,汴京城的空气里浸透了杨柳新芽的清香和御苑百花争妍的馥郁。持续月余的科举风波,随着省试的落幕似乎暂时平息,然而那沉淀在漕运淤泥、贡院砖缝乃至朝堂章奏里的紧张,却如同汛期前的黄河水,表面平静,内里早已涡流暗生。都江堰畔那场以血为祭、惊动星象的“青云血誓”所带来的震荡,虽远隔千山万水,其细微的涟漪已悄然触及了帝国的心脏。
陈砚秋立于金明池畔的宝津楼下,身上崭新的绿绸官袍在煦暖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却熨不平他眉宇间积郁的凝重。川蜀之行,洞悉母亲林氏身世之谜,亲历寒门学子以血明志,更揭破了韩似道及其背后势力试图以“碱草”毒术戕害天下文运的惊天阴谋……这一切,绝非一纸擢升敕令所能轻易抹去。臂弯处,那日血誓留下的青羽纹身隐隐热,并非痛楚,而是一种无声的警醒,提醒着他脚下的青云路,实则是以无数前驱者的白骨与热血铺就。
今日的金明池,因琼林宴而对外开放,万姓游赏,喧声鼎沸。池面楼船彩帜飘扬,岸侧百戏竞呈奇技,卖各色吃食、玩具、时令鲜花的摊贩吆喝声此起彼伏,织就了一幅太平盛世的繁华图卷。新科进士们身着绯袍,头戴簪花,在万众瞩目与羡慕声中,于宝津楼前接受天子赐宴,这是他们人生中最为荣耀的时刻之一。
陈砚秋虽因功得以列席此宴,但他非本届进士,身份尴尬,加之此前屡屡触动科举积弊,在那些谈笑风生、互相道贺的官员与进士圈中,他显得格格不入,如同一个沉默的异类。他冷眼旁观,见那些春风得意的面孔中,既有真才实学之辈,亦不乏早已被墨娘子情报网标记、与“题引”黑市或世家关联甚密之人。盛宴之下,寒门与世家、清流与浊流之间的鸿沟,并未因一场考试而消弭,反而在这极致的荣耀衬托下,愈刺目。
“砚秋兄,独在此处凭栏,莫不是还在思索蜀中风云?”一个清朗的声音自身后传来。陈砚秋回头,见是赵明烛。他今日未着皇城司公服,而是一身月白常服,但那双异色的瞳仁深处,依旧闪烁着监考官特有的审慎与机敏。他手中把玩着一柄玉骨小扇,看似闲适,目光却在不经意间扫过周遭熙攘的人群。
“明烛兄,”陈砚秋微微颔,“蜀中事虽了,余波未平。今日此地,锦绣繁华,倒让人恍若隔世。”他语带双关。
赵明烛轻笑一声,扇骨轻敲掌心:“隔世未必,但确是另一个战场。你看那边——”他以扇梢虚指宝津楼前正在进行的“诗碑”活动。数十名身着彩衣的侍从,每人手持一块巨大的木牌,其上书写着诗词句读,根据司仪的指令,不断移动组合,拼凑出应景的诗词,引来围观士庶阵阵喝彩。
“活人诗碑……”陈砚秋眼神一凝,立刻想起数年前宰相府夜宴那场惊心动魄、暗藏杀机的“行为艺术”。“旧事重演,不知此番又是谁家手笔?”
“听闻是宫中某位喜好风雅的内侍省都都知提议,深合官家之意。”赵明烛压低声音,“韩似道韩相公似乎也颇为赞许,认为可彰显我朝文治之盛。”
听到韩似道的名字,陈砚秋的心猛地一沉。这位掌控科举多年的幕后“提线人”,在川蜀险些功亏一篑后,此刻安然端坐于楼内盛宴之上,其泰然自若,反而更令人觉得深不可测。
宴会按部就班地进行。御酒佳肴如流水般呈上。银质的酒壶、试毒的银筷、侍奉在侧的尝药内侍,一切似乎都遵循着严格的宫廷礼仪与安全规程。陈砚秋注意到,光禄寺的官员们面色紧张,穿梭忙碌,确保万无一失。
酒过三巡,诗兴渐浓。一位身着略显陈旧绯袍的进士站起身来,向御座方向躬身一礼,朗声道:“陛下,今日琼林盛宴,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臣李玮,不才蒙恩忝列科甲,感念圣恩浩荡,亦深感科举之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今有拙作一,愿抛砖引玉,亦祈愿朝廷能持续肃清科场,使寒士皆有晋身之阶,则天下文运必如这金明池水,滔滔不息!”
此言一出,楼内楼外顿时安静了几分。李玮此人,陈砚秋略有耳闻,出身寒微,在士林中以直言敢谏着称,尤其在科举改革方面,多次上书言事,针砭时弊,早已引起某些人的不快。他此刻在琼林宴上作此言论,无疑是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块巨石。
有官员面露赞许,亦有不少人神色不豫,交头接耳。御座上的仁宗皇帝面色如常,微微颔,示意他但作无妨。
李玮深吸一口气,目光扫过在场诸多重臣,开始吟诵他的诗作。诗句铿锵,直指科场积弊,甚至隐晦提及了“墨池浊浪”、“青蝇营营”等语,引得韩似道端起茶杯的手指微微顿了一下。
诗成,掌声稀落,气氛一时有些凝滞。李玮却似毫无所觉,躬身谢恩后,便举步走向那“活人诗碑”的队伍,似乎想亲自拿起一块诗牌,以示与民同乐。
就在他走到诗牌旁,伸手欲取最顶端那块写着“墨池深”三字的木牌时,异变陡生!
李玮的手臂刚刚抬起,忽然猛地一颤,脸色瞬间变得青紫,喉咙里出“咯咯”的怪响,身体剧烈地抽搐起来。他手中那杯尚未饮尽的御酒“啪”地一声跌落在地,酒液四溅。
“啊——!”周围的侍从和近处的进士们出惊呼。
众目睽睽之下,李玮踉跄几步,猛地扑倒在那堆诗牌之上。他双目圆睁,似乎想说什么,右手艰难地抬起,食指颤抖着伸向嘴边,猛地咬破,随即用尽最后力气,在那块“墨池深”的诗牌上,颤巍巍地划下了三道血痕——那似乎是一个未完成的字,或是某个符号的一部分。
随即,他头一歪,气息全无。
死一般的寂静笼罩了宝津楼内外,只有远处百姓游赏的喧哗声隐约传来,更衬得此处的死寂无比骇人。
“护驾!”内侍省都知尖利的嗓音划破寂静,大内侍卫瞬间簇拥到御前。
赵明烛反应极快,异色双瞳寒光一闪,厉声道:“封锁宝津楼!所有人原地不动!崔太医!”他早已安排皇城司的人手混在侍卫和侍从中,此刻迅控制住各个出口,并将楼内人员隔离看守。
陈砚秋一个箭步冲到李玮尸身旁,蹲下身查看。崔月隐不知何时也已赶到,他面色沉静,推开试图上前维护秩序的内侍,迅检查死者瞳孔、口鼻和脉搏。
“中毒。”崔月隐言简意赅,他抬起李玮那只咬破的手指,仔细观察,又凑近鼻尖轻嗅,“指甲缝中有微量紫色结晶,口中有奇异果香,非中原常见毒物。”他目光扫过地上的银质酒杯,“银器未变黑,非砒霜之类。”
陈砚秋的目光则死死盯住那块染血的“墨池深”诗牌,以及李玮未能写完的血字。那未完成的笔画,凌厉而绝望,透着一股令人心悸的诡异。
赵明烛已令人将李玮饮过的酒壶、酒杯以及同桌其他人的酒具全部封存查验。他走到陈砚秋身边,低声道:“光禄寺、内酒坊、内侍省经手饮食之人,一个也跑不了。”他的目光同样落在那诗牌和血字上,眉头紧锁,“墨池深……这像是某种控诉,或是……线索?”
陈砚秋抬起头,望向楼内那些或惊恐、或愕然、或面无表情的官员和进士们,缓缓道:“是控诉,也是挑衅。有人在琼林宴上,天子眼前,用最狠毒的方式,封住了一个敢于直言者的口。”
他的目光越过骚动的人群,似乎想穿透这繁华的帷幕,看清那隐藏在其后的、冰冷而狰狞的真相。臂弯处的青羽纹身,此刻灼热感愈清晰,仿佛在与那未干的血迹相互呼应。
金明池的碧波依旧荡漾,游人的欢笑依旧喧嚣,但宝津楼内,皇佑元年的琼林宴,已被一层浓重的、名为阴谋与死亡的阴影彻底笼罩。一场始于科举、震动朝野的更大风暴,已在这极致的繁华中,露出了它血腥的獠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