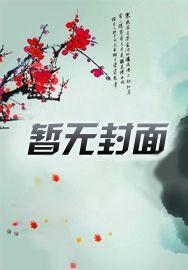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数风流人物还看前世与今朝 > 第329章 八国联军的战役与战术评价(第1页)
第329章 八国联军的战役与战术评价(第1页)
“战略层面的清方立场,我建议由eason待会为大家说明”。戴伟胜显然已经进入了一个向军官团做战争复盘报告的状态,而且泄露了不少秘密。但是,没办法,只要你想说实话,只要你还讲逻辑,那么真相和所谓的秘密是掩盖不了的。当然,这里的秘密是指战后利益分配的分歧之类显而易见、顺理成章的事情。更重要的如战略决心如何下、各国之间的密约等等,不影响顺利表达的,是根本秃噜不出来的。戴伟胜继续道:
“战役层面,我将其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东交民巷保卫战,时间是从6月2o日至7月14日。这期间,估计有义和团民约3万人,含部分清军甘军,包围东交民巷,用土炮轰击使馆。虽造成少量人员伤亡,但未切断水源、电力。联军方面,使馆区守军有各国卫兵约4oo人,加中国教民武装,依托工事坚守,利用电报向天津求援。6月21日,清廷对11国宣战,联军获得“战争合法性”,加从天津调兵,其中英国“亚眠”号运兵船7月5日抵达大沽。
战役结果,义和团的“围攻”沦为消耗战,自身伤亡相信2ooo人,未达成其鼓吹的“灭洋”目标。而联军通过外交施压与军事威慑,迫使清廷内部主和派抬头,为后续军事干预铺路。
第二阶段是天津攻防战,时间是7月14日到8月14日。据信,清军聂士成部“武卫前军”约1。5万人与义和团联合防守天津城,依托城墙、炮台抵抗。义和团在北运河用棺材装火药设“水雷阵”,但因水流湍急未奏效。聂士成部炮击紫竹林租界,摧毁部分洋楼,但因弹药不足未能扩大战果。
联军方面,日军在福岛安正的指挥下担任主攻,利用其近代化装备,如射炮、马克沁机枪,突破清军左翼,7月17日攻占东机器局。英军加德纳少将率印度兵从水路包抄,摧毁清军水师。各国联军因指挥权混乱,日军与俄军甚至为争夺天津站生交火,初期进展缓慢。
战役结果,清军伤亡应8ooo人,其中聂士成战死,义和团被击溃,死伤约5ooo人。联军伤亡仅约2ooo人,其中日军占12oo人,暴露清军主要装备的抬枪、土炮与密集冲锋的战术与联军的代差劣势。
第三阶段是北京攻防战,时间是8月14日至8月28日。清军荣禄率残部退守北京城外,未组织有效抵抗。义和团“乾字团”“坎字团”在广渠门、朝阳门用粪叉、锄头袭击联军,被机枪成片扫射倒下。进攻开始的第二天,我们就收到消息,你们的太后携皇帝仓皇西逃,走前下令“所有官兵均须保护使馆”,说明清方彻底丧失了抵抗意志。
联军总兵力增至1。8万人,其中日军8ooo、俄军4ooo、英军3ooo、美法德各1ooo,分路进攻北京。8月14日,日军率先突破广渠门,英军随后攻占东便门,俄军从永定门入城。各国军队在北京城内分区占领,比如日军占东城、俄军占西城。
期间清军几乎未组织有效战斗,联军仅伤亡约5oo人,其中日军3oo人。
战役方面的评估是:大沽口天津战役期间,联军,尤以俄军为主力初期,展现出强大的两栖登陆和攻坚能力,迅夺取北方门户。但后续天津城内的巷战暴露联军协同问题,进展缓慢且伤亡增加。
进军北京战役规划因各国争吵而一再拖延,给予清军重整时间,尽管清军并未对此加以利用。最终行动中,日、英、美军作为主力,组织尚可。利用铁路-虽遭破坏-和河道进行补给是明智之举。廊坊遭遇战显示联军在野战中面对清军义和团的绝对优势。
北京的攻城战相对顺利,尤其日军表现突出,得益于守军董福祥甘军和义和团士气崩溃和组织混乱。解围使馆是战役高潮,但实际战斗烈度在破城后已显着降低。
后续扫荡缺乏统一规划,各国自行其是,如俄军大举入侵满洲,效率低下且易引冲突。对西逃朝廷未形成有效追击。
联军的优势是强大的工程能力,可以修复铁路、架桥;炮兵火力投射能力;相对良好的战场通讯,包括有线电报、传令兵。
劣势在于战役层面协同依然薄弱。后勤瓶颈始终是制约因素,进军北京时补给困难。对广袤中国腹地的控制力有限。
我的评价是:尽管存在协调问题,联军在关键战役节点上的优势无可辩驳。日本军队在组织纪律和进攻精神上表现优异,值得关注。英国军队,尤其印度部队,在艰苦条件下展现了坚韧。然而,未能彻底摧毁清军主力或俘获其朝廷,为未来留下隐患。扫荡行动的无序浪费了资源。
清帝国和义和团,其围攻使馆区是一场战略和战役层面的彻底失败。拥有绝对兵力优势,包括董福祥部、荣禄武卫中军部分、大量义和团,和地利,却因多头指挥、朝令夕改造成指挥混乱;战术呆板,缺乏有效步炮协同、不敢坚决突击;士兵畏战,尤其是正规军,而久攻不下,最终成为联军进军的口实和自身无能的铁证。义和团的狂热无法弥补其军事上的无效。
天津防御作战中,聂士成部进行了相对顽强的抵抗,但孤立无援,战术陈旧,死守阵地承受炮轰,最终被优势联军击溃。聂的战死是其部队为数不多的亮点。
京津间阻击防御期间,在杨村、廊坊等地组织的防御形同虚设。清军主力,如宋庆、马玉崑部,消极避战,稍触即溃。义和团袭扰造成小麻烦,但无法影响战役进程。北京城墙防御未挥应有作用。
清方无显着战役层面优势。部分指挥官-如聂士成-的个人勇气无法扭转整体败局。
劣势有战役指挥体系完全瘫痪,各部队各自为战,甚至互相拆台,如我们审问俘虏得知裕禄与聂士成之间的矛盾。后勤崩溃导致前线饥馑。部队毫无机动性,被动挨打。对联军行动意图判断完全错误。
我的评价是:“清军的战役表现只能用‘灾难性’形容。围攻使馆是其愚昧与虚弱的集中体现。在野战或防御中,他们缺乏任何近代化军队应有的组织、机动和韧性。义和团在战役层面除了制造混乱和屠杀平民,毫无军事价值。其抵抗意志在遭受真正的现代化火力打击后迅瓦解”。
戴伟胜在接过王月生贴心地递过来的一杯很纯正香味的英国红茶后,点头致谢,同时现,几个中国人,包括刚刚给自己递茶的王月生,都在用一种从来没见过的漂亮的自来水笔和有漂亮的皮革封面的本子疯狂地记录着。其中,郑贯公还时不时地偷瞄一下两边的学员笔记本上的简体字,暗恨不公平,自己要写那么多笔划才写完一个字,那边几笔就完成了。
戴伟胜看了看王月生,见他缓慢地摇了摇头,便知其答应了自己不会向外披露。他自然十分相信王月生,而且盼望着自己抛的军事上的、表面上的砖,能够引来王月生关于政治上的、深层次的玉。所以,他喝了几口茶,补充水分后,继续道:
“在战术层面,我们军人关注武器、指挥与士气的对比。
其中,武器装备的代差决定了战场主导权。
联军方面,英军李-恩菲尔德步枪射程5oo米,日军三十年式步枪射程4oo米,均配备弹仓供弹,每分钟1o—15;
英军75毫米野战炮射程6公里,日军92式重机枪射45o分钟,可压制清军土炮的5oo米射程和每分钟1的射;
后勤上,联军配备野战医院、罐头食品、通讯鸽,日均行军3o公里。
相较之下,清军方面:
占总兵力7o%的义和团仅有刀矛、土枪,清军主力装备抬枪,射程3oo米,需2人操作,老式前装炮装填需1o分钟;
义和团“练拳不练枪”,清军士兵,尤其绿营,缺乏实弹射击训练,部分士兵从未摸过枪;
后勤上清军粮草依赖地方摊派,沿途常因“百姓闭户”断供,如聂士成部在杨村饿死3oo人。依赖粮车运输,日均行军不足1o公里。
在指挥体系上,双方更表现出了纪律与协同的差距。
联军方面,虽各国矛盾尖锐,如俄军擅自占领山海关,但前线指挥官,如日军福岛安正、英军加德纳均接受过近代军事教育,擅长“集中火力、分进合击”;
使用野战电话与信鸽建立了临时通讯网,确保各部队信息同步,如天津战役中,日军通过信鸽告知英军清军左翼薄弱。
清军义和团方面,清军指挥系统混乱,荣禄、董福祥、聂士成各领一军,互不统属,朝廷的“圣旨”靠骑马送信,常因传递延误失去时效;
义和团“坛口自治”,各团领仅听命于本地香主,无统一号令,如北京城破时,部分团民仍在胡同里“练拳”。
在士气与组织方面,再次证明了组织力碾压“血性”:
联军方面,士兵受“解救侨民”、“殖民荣誉”激励,英军士兵高唱《天佑女王》冲锋,军官通过勋章、晋升维持纪律,日军少佐因攻占天津站获旭日勋章;
虽然由于对“敌人”的恐惧转化为“集体暴力”,比如德军士兵因克林德之死屠杀了不少北京平民,但战场纪律总体严明,无大规模溃退。
清国方面,清军士兵,尤其汉军,普遍厌战,俘虏称“打洋毛子是为了保大清,大清却克扣军饷”。临阵脱逃者众,如董福祥部甘军在北京城破时集体溃退;
义和团“刀枪不入”的迷信在实战中彻底破灭,被机枪扫射后士气崩溃,部分团民甚至倒戈协助联军,如西四牌楼团民向日军指认藏匿的清军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