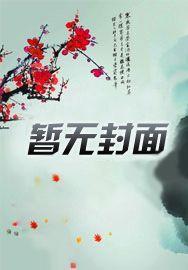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大明:历经六朝,终成大将军王! > 第625章 于谦来了(第1页)
第625章 于谦来了(第1页)
半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
在蓝武的刻意放权和朱瞻基自身的努力下,这位年轻的皇太孙,已经初步在中军护卫营中树立起了自己的威望。
他不再是那个纸上谈兵的少年,每日与老兵们同吃同住,一同在烈日下操练,那份与生俱来的贵气,被沙场的风霜磨砺出了一股逼人的锐气。
而就在整个哈密卫的战争机器,都已预热到极致,只待一声令下便可向北奔涌之时,京城的第二份旨意,终于到了。
这一次,比上次的密旨要正式得多。
凉国公府正堂,香案高设。
蓝武与朱瞻基并肩而立,身后是平安、张奎等一众哈密卫高级将领,众人皆是甲胄在身,神态肃穆。
一名从京城来的太监,展开黄绢,用他那特有的尖细嗓音,高声宣读着。
圣旨的内容,无非是些冠冕堂皇的言辞,先是痛斥了瓦剌马哈木的不臣之心,然后便是正式下达了北伐的诏令,鼓舞将士用命,为国开疆。
这些,都在蓝武的预料之中。
直到那太监念完了圣旨,小心翼翼地将其卷起,然后又从身旁的木匣中,取出了另一卷黄绢。
“陛下另有旨意。”
太监清了清嗓子,再次宣读。
“为正军纪,明法度,朕特遣都察院监察御史于谦,巡按西北,为征西路军监军,总览钱粮功赏,凡有不法,可密折专奏。”
监军!
当这两个字落下时,堂下以平安为的武将们,都是齐齐变了脸色。
大明自太祖皇帝起,便极度厌恶监军制度,认为这是外行干预内行,自毁长城之举。
没想到,这一次北伐,陛下竟然又把这套东西给捡回来了。
蓝武倒是没什么反应,这早在他的预料之中。
太子与汉王在朝堂上的那场争论,他通过自己的渠道,早已知晓。
朱棣此举,既是安抚文官集团,也是为了平衡,更是为了给朱瞻基的军功做背书。
只是,他没想到,被朱棣派过来的竟然是于谦。
当这个名字从太监口中喊出时,蓝武整个人,都罕见地愣住了。
他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
于谦!
是自己想的那个于谦于少保吗?
那个在北京保卫战中,力挽狂澜,扶大厦之将倾,被后世誉为“救时宰相”的于谦?
如果他没记错的话。
这个时候的于谦,应该只是个刚刚考中进士没多久,在官场上还没什么名气的年轻人吧?
不过想想也正常。
都察院的监察御史,官阶不过正七品,虽然职权极重,有巡按天下之权,但毕竟只是小官。
再加上于谦本就极有才华,而且朱棣还知道大明本来的历史,能提前把于谦找出来重点培养,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但说实话,派来监察一路征伐大军,而且是凉国公和皇太孙共同执掌的大军,这分量,是不是太轻了点?
在众人惊疑不定的注视中,一个身穿青色官袍的年轻人,从堂外缓步走了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