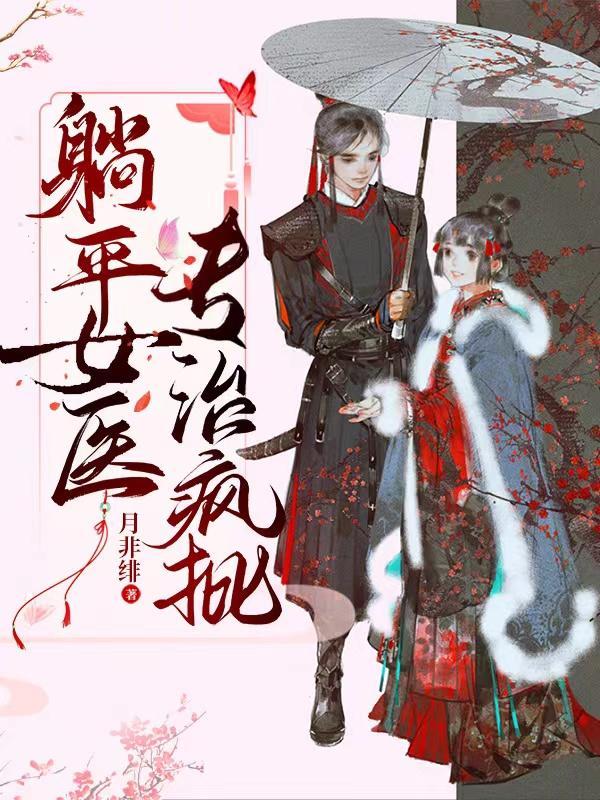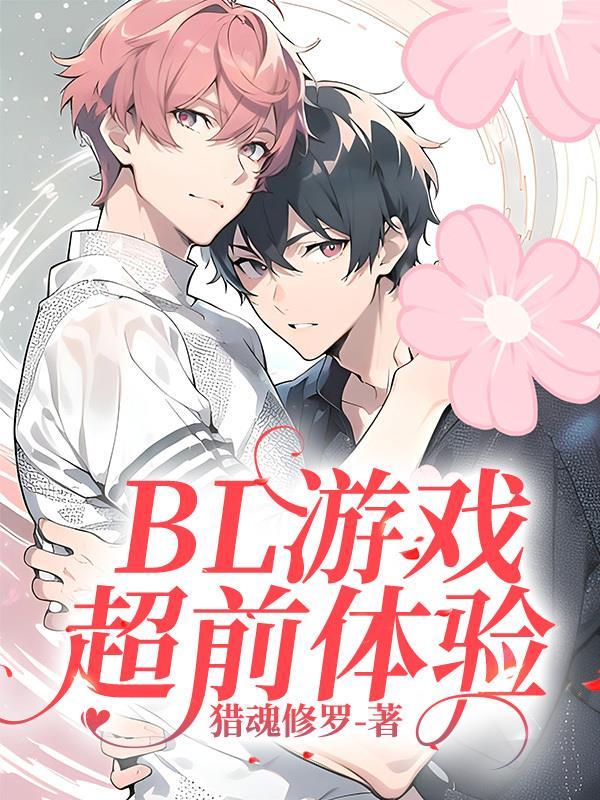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纨绔六皇子,从八岁开始布局天下 > 第568章 万国请柬发四海风雷动(第1页)
第568章 万国请柬发四海风雷动(第1页)
玄京入冬的第三场雪,悄然落在琉璃殿檐。夜色如墨,宫阙深沉,灯火在风中摇曳着,映出金瓦如潮。宁凡站在御书房窗前,目光穿过重重宫墙,落向远处的天街与礼部衙门。那一方灯火未灭,正有人彻夜赶制国书。
雪光映进窗内,照亮案上那封未盖印的圣旨。锦面卷轴上,以金砂描边,玄鸟纹浮动,龙章凤篆间有火影闪烁。那是属于帝王的命笔。
“天子欲令四海宾服,非刀兵之威,而以文明之光。”宁凡低声道,语气平静,却带着一种不可违逆的笃定。
苏若雪执笔立于案旁,素衣掩香,笔锋如水。她抬眸问道:“陛下意在‘万国博览’,此举一出,四方必震,尤以鹰翔与大月为甚。可否担心其反感?”
宁凡淡笑,指尖轻触卷:“反感,正合朕意。”
笔声沙沙,苏若雪继续书写,字里行间满是帝国的自信与包容。她的手微颤了一下,却又稳了下来。她知道,这不仅是一纸国书,更是一场棋局的开端。
窗外风雪愈急。秦如月披着玄绫斗篷步入殿中,手持礼部奏章,俯身一拜:“陛下,礼部与鸿胪寺已草拟邀请册。臣妾亲审译本,鹰翔文、大月文、蛮文皆已齐备。惟请陛下御批定稿。”
宁凡接过册页,翻开第一页。那一行行字,以玄朝官方正楷书就,端正如碑。文中开篇即道:
“天玄历五百二十七年,承和平之泽,睦邻之道,朕命开万国博览,以广文明,以显天和。凡天下之邦,若尊仁政,共利生民,则可同登盛世之台。”
字句雍容,仪态庄严。苏若雪以心血琢磨出的章法,既显天朝气度,又暗藏“顺我者昌”的锋芒。
宁凡的指尖在“共荣”二字上微顿。那金砂反光如火,映出他眸中的冷意。
“秦卿,”宁凡语声淡淡,却透着某种决断的力度,“鹰翔国、大月、乌斯藏三国的国书,由你亲笔润色。”
秦如月抬,微怔。她明白那是信号——一场心理战的开局。
“臣妾明白。”她轻应,眉眼间浮出一抹淡光。
苏若雪则沉吟:“陛下欲分层用辞,小国以怀柔,大国以威仪……此法极妙,只是若言过分厚重,恐被察觉意图。”
宁凡收笔,将朱印轻按在卷上,印章“玄天之玺”沉入金文:“他们若不察,愚;若察,又奈我何?”
一印落,千国惊。
夜色渐深,殿中烛火摇曳,映出几人影子交叠。那是文明与权力在火光中的形状。
——
翌日清晨,礼部大门外雪已停。天街铺上青石板,晨曦映照下泛出微光。文吏成列,衣襟整齐,抱卷待命。
礼部尚书杨敬跪呈金匣:“陛下,国书三十六份,皆经文渊阁、鸿胪寺三署合审。请陛下御封。”
宁凡步出金辇,御袍曳地,玄金冠下的目光冷静如镜。他未言,只抬手示意。内侍捧上“火印”之章,印面玄鸟衔焰,一印落下,封蜡如血。
朱印封合的刹那,群臣齐拜,呼声震街。
“谨奉天玄旨意——”
国书启,四海风动。
——
三日之后,鸿胪寺西门外,三十六名驿骑列阵,披铁甲、执旌节。每人肩负国书一匣,封有朝印。
号角声起,天街百姓纷纷聚观。孩童伸头,商贩低语,人人皆知,这一刻意味着玄朝以天子之姿,正式向四海宣言。
“天朝国书矣!”
鼓声滚滚,旌旗猎猎。驿骑分道出京,南向琅岐,北奔苍原,西去雪岭,东赴海疆。
雪未尽化,蹄声如雷。马背上的金匣在阳光下闪耀,似火似星。
宁凡立于承天门高处,俯瞰人流奔涌。风起,衣袍猎响。苏若雪立于阶下,低声言:“陛下,此举一出,天下当惊。”
宁凡道:“惊,不足惧。惟若天下不惊,朕方忧之。”
——
而在千里之外,鹰翔国宫殿深处,金鹰旗猎猎作响。
国主哈洛坐于议政厅中,接过那封以玄朝文字书就的国书,指尖微颤。
“天玄皇帝宁凡——”他低声念出那个名字,语调中带着复杂的压抑与警惕。
他身旁的鹰翔学士翻阅译本,神色渐凝:“陛下,此书文辞之盛,乃我所未见。其言外之意,似邀非邀,实逼非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