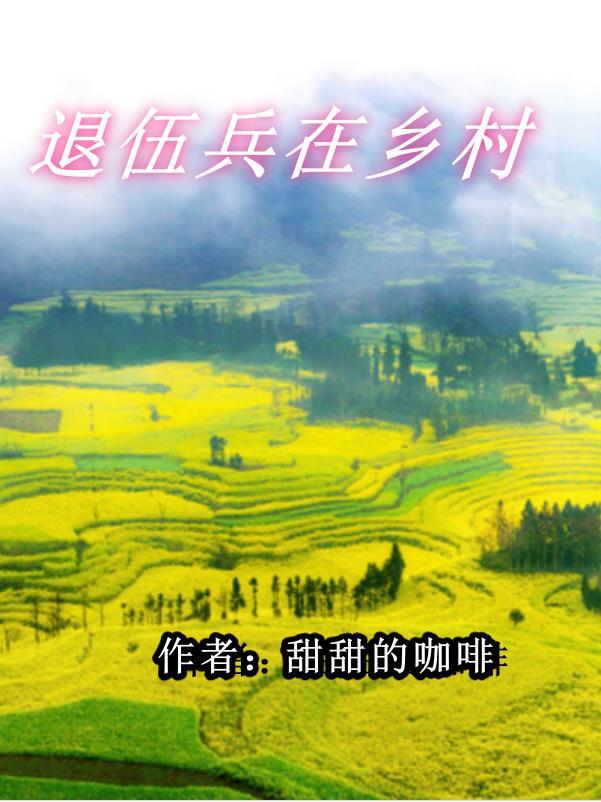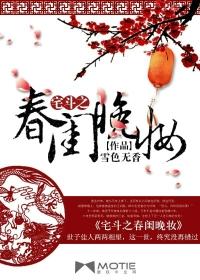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纨绔六皇子,从八岁开始布局天下 > 第563章 海药添新方医典集大成(第1页)
第563章 海药添新方医典集大成(第1页)
东海风浪息后,秋阳初上。
穆烟玉率船归航的那日,京城太医院外,银杏叶正黄,宫墙映日,光影层叠。
她一袭海蓝长衣立在廊下,身后船队缓缓靠岸,箱笼堆叠如山。那是自海外诸岛运来的珍奇药材,气息混合着盐风与异香,扑面而来。
守候多日的太医署官员与药童奔走相迎,眼底闪着难掩的好奇。
“此木名曰金鸡纳,治疟奇效。”穆烟玉指着木箱,语声清朗。箱内木皮色红如血,隐透苦香,“彼邦之人称其为‘命树’,可退热消疠。”
陈御医俯身查看,手指微颤:“果真如此奇异?”
穆烟玉微笑:“此物得之不易,舟覆三次,方保此数篓。”
她的眸色淡淡,像看着远处的浪。自东海一役后,她对波涛的敬畏,已化作一种深藏骨髓的平静。
箱盖一一揭开,随风飘出的,还有一种未被命名的文明气息。
太医院内,苏若雪与秦如月皆至。
“这批药材若能成功引种,玄朝医道,或将更上一层。”苏若雪轻抚案上方卷,眼底的光沉静如镜。
秦如月点头,目光落在药圃之外的花木上:“医者仁心,不问出身,草木有灵,不分南北。若能共植一圃,天下百病皆可疗。”
宁凡此时已在御书房批阅新章,听闻此事,特降诏令:“着太医署设‘海外药圃’,与格物院共研其性。”
自此,玄朝医道正式纳入海外药理。
药圃选址于城南温泉谷,谷地四面环山,气候温润。
三月后,新圃建成。
青瓦白墙之间,雾气蒸腾,药香氤氲。来自蛮荒、西南、东海的草木共生一园,绿影叠翠。
李子清亲自操持引水渠渠,利用新式机闸调节湿度;工部匠人以玄石铺渠底,使泉水恒温。
那一日,宁凡携苏若雪、秦如月、穆烟玉、尘妤一同至药圃巡察。
晨风拂动朱袍,药圃中的万叶微颤。
一名年幼药童正俯身整理药草,抬头之际,恰见帝影。少年怔住,手中的竹匾险些滑落。
宁凡俯身接住,微笑:“慎之为医,贵在心稳。”
少年脸红,连连叩。
穆烟玉莞尔:“陛下之言,胜十载训诲。”
他们在园中徘徊良久,至一株叶片奇异的藤前停步。
藤蔓盘绕石栏,叶色呈蓝绿相间,叶脉闪着微光。
“此名光叶藤,汲海气而生,夜可自明。”穆烟玉低声道,“我观其性,与地南的龙舌草相克相辅,可合为方,治骨热之疾。”
秦如月听罢,已在袖中掏出方帙,飞快记录。
尘妤则看向山脚的溪流,轻声道:“昔日我蛮地巫医以风草疗伤,今观此药,似得神启。海陆之药,各有灵根,世道之通,莫过如此。”
宁凡颔,低声答:“天人之理,不止一途。若能并观并用,天下可医。”
苏若雪立于一旁,默然注视这一幕。风过她鬓角,拂起墨。那一瞬,她忽感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定——那是数十年风霜洗炼后,终于见证文明归心的宁静。
次月,太医署与格物院联合召开“新药论证会”。
药圃外帐篷连绵,旗帜飘扬。来自天下各州的医官、工匠、学士汇聚于此,论药、验方、比试手艺,声如潮涌。
有医者以海药熬膏,色如琥珀;有工匠以铜管试蒸馏,雾气如织。
夜色降临,灯火万盏,犹如星河坠入谷底。
苏若雪亲自主持会议,手执新修《药典》初稿,朗声道:“自古医者多以传口之方,今我朝定篇成典,凡药皆录,凡方皆审,凡效皆验,此为万世医经。”
台下掌声雷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