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五小说网>三国:结拜关张,开局灭黄巾 > 第725章 民账无印岂可为凭(第1页)
第725章 民账无印岂可为凭(第1页)
指尖抠开表层,拨开碎草,露出底下半截竹片边角。
他瞳孔骤缩,喉头一滚,忽然翻身下马,单膝跪地,用匕尖小心剔去浮泥——竹片背面,竟用极细朱砂点了一星小点,位置、大小、晕染弧度,与三年前皓记酒馆后院那排防伪酒坛底部的“朱砂钉”分毫不差。
陈皓教过的。
那时柱子还扎着冲天辫,踮脚够酒坛,陈皓把他拎下来,按着他的手,在坛底刻下第一道凹痕:“酒坛会碎,坛底的印子,得长进土里才作数。”
如今,印子真的长进了土里。
消息传得比山风还快。
不到午时,工棚外就聚起二十余人,有昨日刚领了工钱的少年,也有扛着锄头来送饭的老妇。
他们不说话,只盯着李少爷埋竹片的地方,眼神浑浊又灼热,像盯着一口刚凿出水的井。
有人嘀咕:“孙家公子昨儿去了县学,听说捐了五百贯,要修《功德录》……说塌桥是流犯监工失察,连图纸都是错的。”
话音未落,一个孩童攥着炭笔跑来,指着远处山坳——那块为古渠湮没而立的无字碑,昨夜还画着蜿蜒沟渠线,今早却被人用湿泥抹去大半,只余断续几笔,歪斜如垂死蚯蚓。
人群静了一瞬。
老汉拄着拐来了。
他没看碑,也没看人,只盯着李少爷手里那本山藤纸日志,封面三枚靛蓝铜钱印,在日光下泛着沉哑光泽。
他伸出手,枯枝般的手指悬在纸页上方,迟迟未落。
“若信我,”李少爷忽然开口,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青石,“明日随我去挖。”
没人应声。
可次日卯正,渡口段路基旁已站了三十七个人。
锄头、铁钎、豁口陶碗,全都攥得死紧。
李少爷没指一处,只翻开日志暴雨夜那页,指尖停在一行小楷上:“申时三刻,南坪第三导流口下三尺七寸,土色褐中泛青,触之微黏,刮之有茶渍气。”
他抬眼,望向张大叔:“您家去年春焙的‘雾岭毛峰’,炒青时火候偏重,叶底泛褐,泡汤后盏沿留渍——那渍,就是这个味。”
张大叔一怔,下意识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喉结上下一动。
众人挥锄。
第一处,掘开三尺七寸,泥色果如所载,褐中泛青;刨开湿土,赫然露出一枚竹片,刻着“三月廿六,晴,风南”,背面朱砂点,与日志页眉批注的“试水ph值”墨迹旁所绘色卡完全一致——靛蓝浸醋、褐黄遇碱、惨白近酸,而那竹片边缘沾着一点干涸茶渍,正是雾岭毛峰特有的褐中透赭。
第二处,第三处……皆准。
当最后一片竹片被捧出时,泥水顺着指缝滴落,日志摊在众人围成的圆心,纸页被山风掀得哗哗作响。
墨迹未洇,字字如钉。
就在此时,马蹄声自东而来,不疾不徐,踏在未干的泥路上,出沉闷回响。
陈皓到了。
他未披斗篷,青布直裰沾着晨露,肩头落着两片松针,针尖凝着北岭山脊特有的铁锈色露珠。
他跳下马,目光扫过众人手中泥污的竹片、摊开的日志、还有李少爷低垂的颈项——那里,一道旧疤蜿蜒如蛇,是万记酒坊板子留下的,如今覆着新结的痂。
他没看那本日志,也没赞一句。
只上前一步,伸手,从李少爷掌中轻轻抽走那页暴雨夜的记录,纸角微颤,墨迹在风里簌簌欲飞。
然后,他抬起眼,目光如刃,直刺李少爷瞳底:
“若日志被焚,路还能不能说话?”
李少爷一怔,喉结猛地一跳。
陈皓却已转身,袍角掠过众人脚边,朝古渠旧址方向走去。
李少爷下意识跟上。
山风忽烈,卷起满地枯叶与尘土。
他们停在一处坍塌的渠壁前。
陈皓抬手,指向青黑苔痕密布的石缝——那里,一道极细的水线正悄然渗出,在晨光里泛着微不可察的银光,蜿蜒向下,无声汇入归源道主路基底。
苔痕之下,石面隐约可见几道浅浅刻痕,形如箭头,指向同一方向。
李少爷屏住呼吸,俯身细看。
那刻痕边缘,竟也嵌着半粒风干的茶渍。
陈皓的手指离开那页暴雨夜的记录时,纸角在风里绷成一道微颤的弧线,像一张拉满却未放的弓。
李少爷喉间紧,仿佛被那句诘问攥住了气管——“若日志被焚,路还能不能说话?”
不是赞许,不是嘉许,甚至不是确认。
是叩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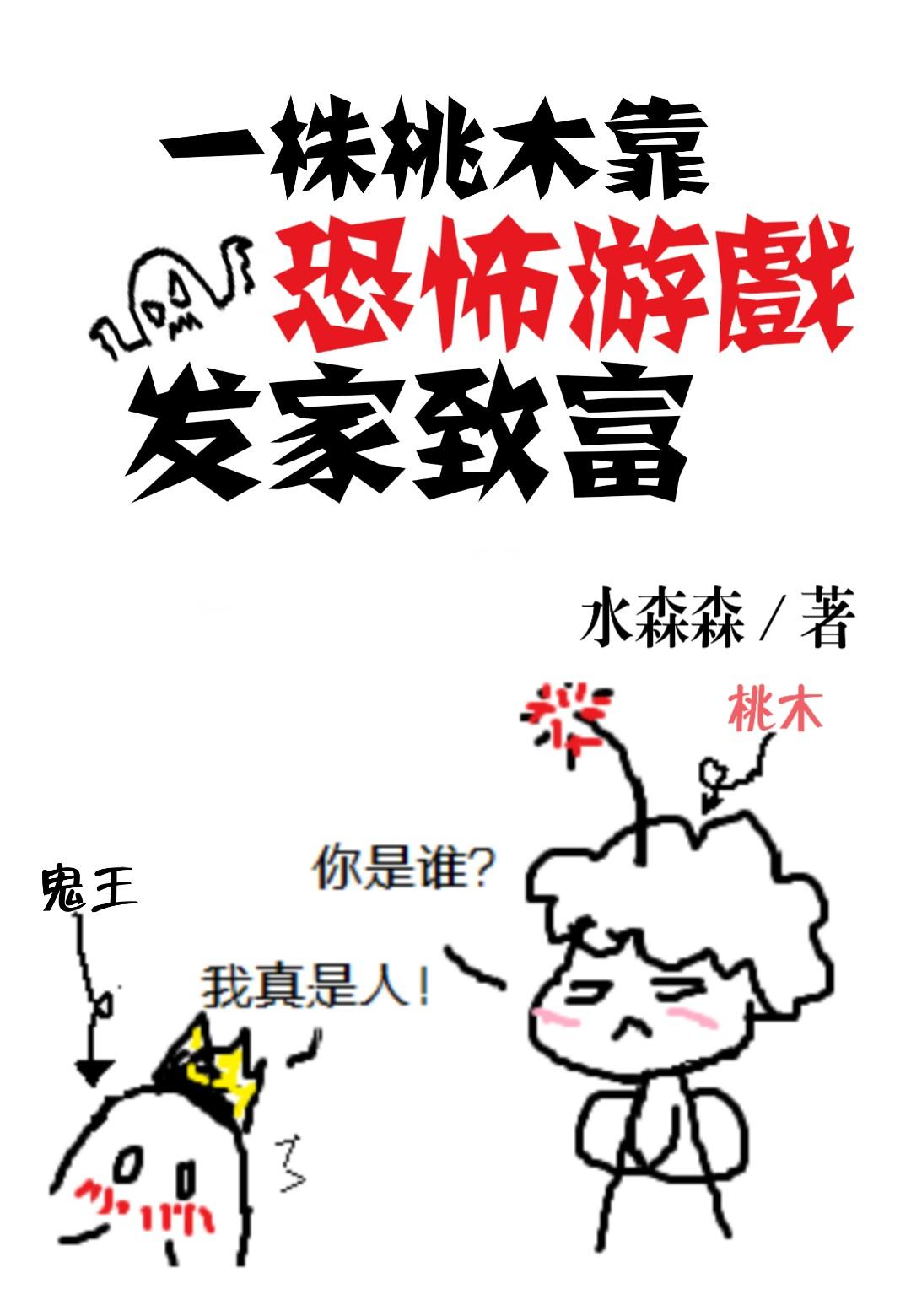

![(柯南同人)[诸伏景光]2号花瓣+番外](/img/35207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