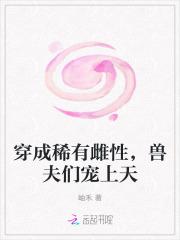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手搓弓弩养娇妻,竟要我黄袍加身 > 第262章 说徐公(第1页)
第262章 说徐公(第1页)
从武安侯府出来,秦福亲自驾着马车送三人回镇北侯府。马车行至侯府门口,秦福恭敬地搀扶林月颜下车,又对陈锋道:“公子慢走,侯爷吩咐了,有事随时差人来说一声。”
陈锋点头致谢,目送马车离去。叶承站在一旁,还有些恍惚。他眉头微蹙,似乎还在消化上午那场信息量巨大的谈话。偶尔抬眼看向陈锋,眼神里除了敬畏,还多了一丝难以言喻的复杂。
他想起大哥在演武场上侃侃而谈的模样,想起秦元那句“你这脑子是怎么长的”,心中既自豪又有些酸涩——原来自己一直引以为豪的“大哥”,早已走在了比他想象中更远的路上。
“三弟,怎么了?”陈锋见他神情呆滞,笑着问道。
叶承猛地回神,挠头道:“大哥,我……我刚才还在想,秦叔说要将那一成利全部用于边军,连侯府开销都不能动。这……这也太狠了!可我越想越觉得,秦叔不愧是军中泰斗,眼光比咱们长远太多了!”
陈锋拍了拍他的肩:“秦叔心里装着的是数十万将士,岂会为一己之私?”
“武安侯爷,的确是国之柱石,心怀天下。”她轻声道,手指轻轻抚平陈锋直裰上的褶皱,“夫君能得他如此看重,是夫君的福气。”
随即,她又有些担忧地看着陈锋:“只是……徐爷爷那边,他一生清高,最是厌恶商贾之事。我们此去,将这充满铜臭味的计划说与他听,他……会同意吗?会不会反而觉得夫君你……不务正业,被俗务所染?”
陈锋握住她的手,掌心传来的温度让林月颜心头一暖。
“放心。对什么人,说什么话。对武安侯这等杀伐决断的军中统帅,我们便要直抒胸臆,谈军国大计,论利弊得失。”
“而对徐爷爷这等一生风骨的文坛泰斗,我们便要……谈风雅,论文脉传承,让他看到这俗事背后,那份对读书人的尊重与扶持。”
林月颜看着丈夫眼中的光,心中的忧虑散去大半。她知道,这个男人总能在看似无路之处,辟出一条坦途来。
“奴家信夫君。”她低声道,从袖中取出一方素帕,轻轻为陈锋拭去额角细微的汗珠,“只是……徐爷爷最重清名。咱们带去的礼物,还需再斟酌斟酌。”
陈锋点头。早先准备的谢礼是一盒上等徽墨,此刻看来,怕是不够分量。
林月颜从随身的布包中取出一个布卷,打开来,是一卷手抄的《孝经》。纸张泛黄,显然是用书院后山晾晒的竹纸所制。字迹娟秀工整,每页边角都有细致的注释,笔锋圆润中带着骨力,显是抄录时下了极大功夫。
“这是奴家这几日抄的。”林月颜解释道,指尖轻抚过纸页,“徐爷爷一生以孝治学,最重《孝经》。奴家不仅抄录正文,还将历代大儒的注解,择其精要,附于页边。又在卷末,附了自己一点浅见……”
陈锋翻看几页,见注释处字字珠玑,既有对经义的深刻理解,又有结合时局的独到见解,不由得赞道:“月颜,你这注解,比市面上的通行本还要精到。徐爷爷见了,定会欢喜。”
林月颜脸颊微红:“哪里。不过是些浅薄之见。只望能入徐爷爷法眼。”
叶承凑过来看了一眼,咋舌道:“嫂子,你这字……比我当年在私塾练的强一百倍!这注解也写得……啧啧。”
“三弟莫要取笑,奴家的字哪有夫君的好看。”林月颜轻笑着将卷轴重新卷好,用素绸系好,“不过待会儿见了徐爷爷,还需三弟多帮衬。你素来爽直,徐爷爷最是喜欢。”
叶承挺起胸膛:“嫂子放心!俺……我一定把话说得妥妥帖帖!”
陈锋与林月颜相视一笑。
一行三人乘上镇北侯府的马车,向城西的长安书院行去。
马车缓缓驶过朱雀大街,街边店铺林立,人声鼎沸。叶承掀开车帘一角,看着外面繁华景象,忽然道:“大哥,你说咱们这会所,真能办成?”
陈锋笑道:“有何不能?谢夫人有商路,秦叔有威望,徐爷爷有文名。咱们集齐了天时地利人和,何愁不成?”
“可我还是担心,”叶承挠头,“徐爷爷最是清高,听说他连朝中大臣的宴请都不去。咱们跟他说开酒楼的事,他会不会……”
林月颜温言道:“三弟莫急。徐爷爷虽清高,却也知‘仓廪实而知礼节’的道理。只要咱们说得在理,他定会明白其中深意。”
说话间,马车已至长安书院大门。
三人下车,院内往来穿梭的学子们见到陈锋,纷纷主动停下脚步,拱手行礼问好,态度恭敬,眼神中带着钦佩之色。
“陈兄!”一个清朗的声音传来。裴宽从一丛修竹后快步走出,脸上带着见到故人的欣喜。他今日穿着一身半旧的青布直裰,袖口还沾着几点墨迹,显然是刚从书斋出来。
“裴兄。”陈锋见礼,“正想找你叙叙。”
裴宽目光扫过林月颜和叶承,略显拘谨地拱手:“这位想必是陈夫人?久仰。”又转向叶承,“这位……”
“这是叶承,我三弟。”陈锋介绍道,“这位是裴宽裴兄,与我在书院论道时结识,学问精深,为人敦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