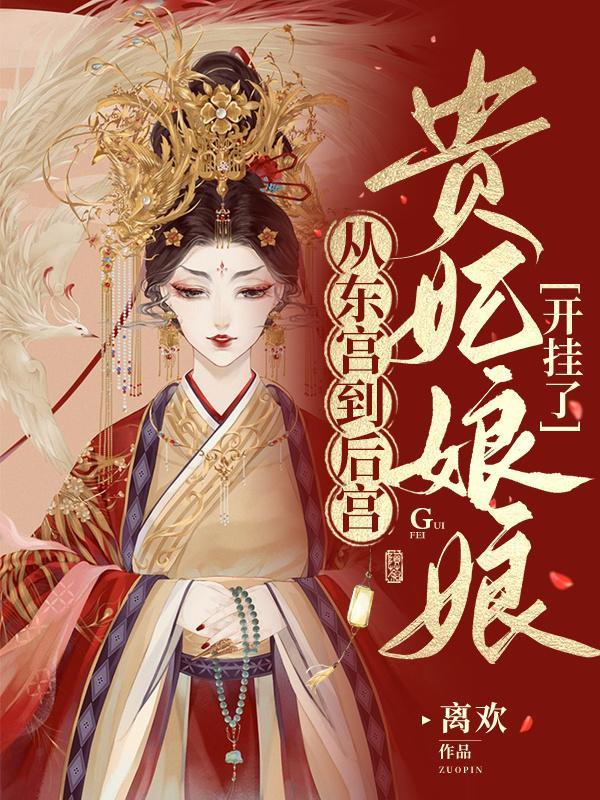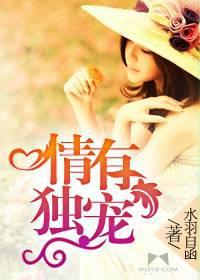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算鼎三国:玄镜红颜录 > 第645章 潜龙入渊初探南郑(第1页)
第645章 潜龙入渊初探南郑(第1页)
脚下的泥土终于变得不再那么松软泥泞,空气中弥漫的水汽也似乎淡薄了些许,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为干燥、带着山林草木清冽气息的风。
我知道,我们已经跨过了那条无形的界线,真正踏入了汉中郡的地界。
回望来路,那蜿蜒崎岖、几乎是硬生生从密林与峭壁间开辟出来的隐秘小径,此刻已被暮色和山岚悄然吞没。
即便是白天,若无熟悉路径之人引领,也断难寻觅其踪迹。
这一路行来,自离开江州之后,我们便彻底化整为零,如同一滴水融入江河,从刘备主力军的视野中彻底消失,
然后沿着玄镜台预先勘探出的最为险峻、也最为隐蔽的路线,日夜兼程,潜行北上。
风餐露宿,跋山涉水,个中艰辛,自不必言。
即便是孙尚香这样自幼习武、体魄强健的江东虎女,眉宇间也难掩一丝疲惫;
更遑论徐庶这等文士,若非意志坚韧,恐怕早已支撑不住。
然而,当真正踏上这片承载着我们未来希望与野心的土地时,所有人的眼中,都重新燃起了光芒。
疲惫被一种难以言喻的兴奋和紧张所取代。
“主公,前方再行约三十里,便可遥望南郑城廓了。”
石秀如同鬼魅般从前方的林木阴影中闪出,声音压得极低,气息却异常平稳,显然经过了长途奔袭和细致侦察。
他身上沾满了尘土和草叶,眼神却锐利如鹰隼,
“依照我们之前的计划,已在城西五里处,找到一处废弃的猎户窝棚,背靠山岩,前有密林遮蔽,暂时可供落脚。
周围我也已查探过,并无明显人迹,只有些许野兽踪迹。”
我点了点头,示意队伍跟上石秀,向那处临时据点行去。
队伍中,除了徐庶、孙尚香、石秀、老吴这几位核心成员,
其余皆是玄镜台的精锐骨干和从锦帆卫中精挑细选、绝对忠诚可靠的悍卒,
以及老吴亲自统领的那支人数不多但战力惊人的亲卫。
总人数不过数百,但每一个都是以一当十的好手,
更重要的是,他们都经过了严格的保密训练,纪律严明,令行禁止。
这是我敢于行此险招,奇袭汉中的底气所在。
夜幕彻底降临,我们在那处简陋却足够隐蔽的窝棚安顿下来。
篝火不敢生得太旺,只用碎石围拢,燃起一小簇,勉强驱散山间的寒意,也足够烤热随身携带的干粮。
石秀摊开一张用特殊墨水绘制、细节极为精准的地图,
这是玄镜台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结合早年间隙传回的情报与近期通过各种渠道渗透、侦察所得的最新成果。
南郑城池的轮廓、主要街道、城防布置、军营分布,
甚至是一些重要的宗教场所(五斗米教的治所、祭坛等)都标注得清清楚楚。
“南郑城防,看似严密,实则外强中干。”
石秀指着地图上的几个点,
“张鲁久在汉中,不思进取,城墙虽高,却多有年久失修之处。
守军看似数量不少,多为五斗米教徒组成,号称‘鬼卒’,平日里受教义约束,颇为顺从,
但真正的战阵之能,据我们观察,远不如中原或江东的精锐部队。
其战斗意志更多依赖于宗教狂热和对祭酒们的盲从,一旦核心指挥被打乱,极易溃散。”
“五斗米教的统治根基,在于其遍布城乡的‘治’,以及那些被称为‘祭酒’的各级神职人员。”
徐庶接过话头,他的声音带着一丝凝重,
“他们以符水、祷告为人治病,收取五斗米,聚拢信徒,形成了一个独立于朝廷法度之外的社会体系。
在汉中,张鲁与其说是一个太守,不如说是一个政教合一的领袖。
百姓对其敬畏有加,这既是他的力量来源,也是他的弱点所在。”
我静静地听着,目光扫过地图,脑海中将玄镜台传来的文字情报与石秀的口述、以及地图上的标注一一对应。
这几日,通过潜伏在城郊的玄镜台暗桩传回的零星信息,我对南郑的氛围有了一些更直观的感受。
这座城池,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安静。
一种不同于战乱地区萧条死寂的安静,也不同于繁华都市喧嚣落幕后的宁静。
那是一种仿佛被某种无形力量规训过的、带着压抑感的秩序井然。
街道上往来的行人,许多都穿着朴素的衣服,神情肃穆,少有喧哗。
偶尔能看到一些身着特殊服饰(或许是祭酒或其从属)的人走过,路人无不恭敬避让。
城中似乎随处可见悬挂着的符箓,或是小型的祭坛,空气中隐隐飘散着若有若无的香烛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