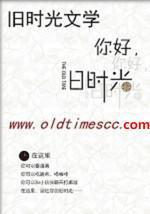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燕山血旗:开局千户所暴杀天下 > 第526章 人事即政治(第2页)
第526章 人事即政治(第2页)
炭盆烧得旺,空气里飘着茶香和戏词的调子。
司马藩急得在屋里转圈,锦靴踩在波斯地毯上,留下浅浅的印子。
他看着坐在檀木椅上听戏的父亲,终于忍不住开口:“爹,诸葛明那老东西都递了三回拜帖了,您何必一直晾着他?再耗下去,对咱们也没好处!”
司马嵩端起青瓷茶杯,吹了吹浮在表面的茶叶,语气淡得像水:“怎么?急着想要回你户部尚书的位置?”
“本来就是我的位置!”
司马藩没藏着掖着,语气里带着不满,“当初要不是因为英国公战败牵连避嫌,我何至于被罢官?
虽然借着扶桑白银回了官场,现在也不过一个微末小吏,现在风头彻底过了,难道不该还我?”
“你啊,终究是眼皮子浅。”
司马嵩缓缓放下茶杯,眼神里的失望藏都藏不住,“一个烂摊子的户部尚书就把你魂勾住了,成不了大事。”
司马藩愣了愣,随即狐疑道:“难道爹您想借机扳倒诸葛明?
可妹妹……太后她不会同意的!
我差人进宫探了口风,她如今是还政躲清闲了,跟您这个亲爹、我这个亲哥都生分了,反而护着个外人诸葛明那老东西!”
“这种事你居然差人入宫问?”
司马嵩瞥了他一眼,语气里带着几分鄙夷,“若绰儿是男子身,你这头蠢猪是女子,才是我司马家的大幸。
你若有她一半的手腕和见识,我何至于一年过古稀还得亲自下场去斗?”
司马藩的脸“唰”地红透了,从脸颊一直烧到耳根,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父亲的话,像根针,扎在了他最痛的地方。
他从小就活在妹妹司马绰的天才光环下。
妹妹虽为女子却七岁能诗,十岁代母亲掌家,十二岁就在内宅宴上驳倒三位当朝学士,被人称作“大魏第一才女”;
而他呢?资质平平,哪怕拜了许多名师大儒,也是直到三十岁才勉强考中举人。
那时候父亲在朝中地位不似如今,政敌环伺,就算妹妹已是贵妃,也不敢在科举上动手脚授人以柄。
他以为考中举人,总能得到父亲一句夸奖,可父亲只冷冷看了他一眼,扔下句话:
“滚去国子监吧。
三十岁才得个末流举子,平日里尽琢磨些小聪明,做不得大文章,再磨二十年你也考不上三甲。”
那句话像根刺,扎了他十几年。
考中举人入国子监,等于公开承认自己是科举失败者——他连一次会试(春闱)都没参加,就被父亲判定“没希望”,直接丢进了国子监。
入国子监对别人来说是天大的恩典,但也是对他寒窗二十年励志科举正途的羞辱。
后来哪怕入了官场,做到户部尚书、进了内阁,也始终有人碎碎念“拼爹”“拼妹妹”的举监罢了。
户部里那些科举正途出身的官员,表面上对他恭敬,背地里谁不笑话他?
这就像高考只考了三本,哪怕后来读了985研究生,第一学历也永远是抹不掉的短板——大企业筛选简历时,第一学历不合格,连看都未必多看一眼。
他无数次想,要是自己像妹妹那样有天赋就好了;
可他在父亲眼里只是个有点小聪明、懂人情世故的庸才,是块朽木。
他比谁都清楚,若妹妹司马绰是男子身;
那他这个长十岁的兄长,早被父亲毫不留情地丢回苏州老家,当个管田产生意的富贵闲人,根本没机会留在金陵的权力中心。
暖阁里的戏还在唱,咿咿呀呀的调子飘在空气里,却没让司马藩的心情好半分。
他看着父亲平静的侧脸,看着父亲手指跟着戏词节奏轻轻敲着扶手;
忽然觉得,自己可能永远也看不透父亲的布局,半生都得不到一句夸赞。
司马嵩像是没注意到儿子的失落,目光落在戏台子上,心里却算得清楚——诸葛明想保住张白圭的吏部尚书之位很难,对方巡盐犯了众怒。
至于儿子的抱怨,他压根没放在心上:庸才需要打磨性子,没得选,别自己自作主张闹笑话就行。